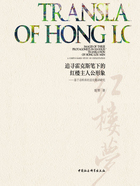
导论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清)得舆
一 选题缘起
(一)《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红楼梦》是“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象征中国整个文化的作品”[1],“古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有《红楼梦》这样丰盈的文化包容量。我们从《红楼梦》里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可以说尽在其中了。《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流露的文化精神,很多可以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2]。《红楼梦》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不仅表现于生活物质等有形物的直接描写中,而且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性格特征的描写,来表现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在我国,以研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为己任的“红学”,成为十分热门的学问,“与‘甲骨学’和‘敦煌学’并称我国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大显学’”[3]。
作为“整个中国文学里最流行的书”[4],《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毋庸置疑。
近年来,对于《红楼梦》英译的研究,人们或引用借鉴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即文艺美学的理论;或采用西方翻译理论,如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或运用当代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前人对《红楼梦》的研究从视角上讲可以归纳为文化学视角[5]、语言学视角[6]和接受美学视角[7]三个研究视角,凸显出多学科研究的特色,我国《红楼梦》英译研究进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不少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加强。“但是仍然有重复选题,甚至重复思路,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8]
对1980—2003年20多年中13种外语类期刊上刊登的所有有关《红楼梦》英译的50篇文章[9]、1980—2006年26年中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登的所有以《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的52篇文章[10]以及1979—2010年30年中CNKI期刊上刊登的所有以《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的782篇文章的分析结果,证实了《红楼梦》英译研究在选题方面存在不足和缺陷。
到目前为止,《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翻译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语料库研究方法兴起之前,情况已然如此;在语料库研究方法兴起之后,也鲜少有人问津这一领域。自1979年至2010年,人物形象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章只有七篇”[11]。
《红楼梦》被誉为一座艺术丰碑,而人物形象塑造是成就这座艺术丰碑的关键。“据统计,《红楼梦》里共描写了774人,有名字或有绰号的,如果连没有名字的也算上去,就有975人。”[12]上至皇帝妃子,中有国公大臣、各级官员衙役,下至仆人丫鬟、市井走卒、村夫村妇,各色人等。“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13]其语言鲜活生动,让人如睹其况,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曹雪芹怀着深挚的情感和同情,用他的诗情画意,用饱蘸着他全部美好理想的笔墨,塑造了一群集“山川日月之精秀”的红楼女儿。翻开《红楼梦》,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就会向我们走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数不胜数的人物以其个人的风采各呈异彩,展现给读者的有宝玉的怪诞、黛玉的任性、宝钗的贤淑、湘云的憨直、凤姐的泼辣、袭人的柔顺、晴雯的率真、可卿的妩媚、探春的果断、惜春的才情、妙玉的孤芳、宝琴的艳丽、香菱的秀逸、鸳鸯的刚直、紫鹃的慧诚和平儿的坚忍,等等。其笔下人物“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迥然有别又栩栩如生。
以《红楼梦》人物形象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红楼梦》英译研究中属于新兴话题,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查,国内最早可以追溯到《从文学文体视角看林黛玉形象在翻译中的再现》[14]。
从那时算起迄今,相关文章数量极为有限,研究零散难成系统,专项研究更是门可罗雀。下面从文章、专著、学位论文三个方面逐一观之。
1.文章情况
相关文章笔者搜集到11篇,作者、题名等信息见表0-1。
表0-1《红楼梦》人物形象翻译论文

11篇文章内容介绍如下:
(1)《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意义显化翻译考察——以霍译本林黛玉人物特征为例》通过对《红楼梦》的霍译本与其所据原著程乙本进行平行语料库的源语/目标语语际对比和分析,考察《红楼梦》霍译本中有关林黛玉人物描写的翻译特征。语料库研究表明:对林黛玉的人物特征,霍译本以释意、增添等方式进行意义显化翻译。
(2)《〈红楼梦〉英译审美中人物外貌的再现与缺失》就《红楼梦》的英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对人物外貌词汇的重组、外貌词汇的模糊化翻译、外貌词汇差异的误读和外貌审美差异下的增译,说明了译者强烈的审美心理活动对文学翻译起着重要影响。
(3)《不同的译者不同的形象美——以〈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文学形象再现为例》就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在再现《红楼梦》中主人公林黛玉的外貌美、服饰美和语言美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所塑造出的林黛玉的文学形象美进行了探讨。
(4)《从人际功能评析〈红楼梦〉英译文的人物形象》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对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及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人物形象以其中的人际意义模型进行了语篇分析研究。
(5)《浅谈〈红楼梦〉茶文化翻译与人物性格塑造》选取其中两个主人公——黛玉和妙玉之于茶事对霍、杨两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借述茶事刻画人物形象,表明人物身份地位、体现人物复杂关系、显示人物学识修养、塑造深化人物性格。
(6)《简析霍克斯英译版〈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的裂变》选取霍译本其中有关林黛玉人物形象翻译实例,认为经霍克斯的翻译后,我们很难再从中复原出那个拥有着高贵气质、温文尔雅的林黛玉形象,留在我们脑中的更多的是活泼、张扬、泼辣、野蛮又略显强悍的黛玉形象。
(7)《〈红楼梦〉外貌英译的审美建构》以《红楼梦》英译本中人物外貌的英译为切入点,探讨分析审美趣味、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作用下译者对人物外貌英译的重新建构与变异现象,认为杨译本的译者与源语文化背景相同,所以更重直译,其笔下的人物外貌英译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审美趣味;而霍译本由于受西方审美意识和态度的影响,更重意译,导致了译本中人物形象的变异。
(8)《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选取七例对比和分析《红楼梦》的霍、杨两英译本,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杨译本中尽可能尊重原文和原文文化,霍译本考虑更多的是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
(9)《杨译〈红楼梦〉中王熙凤语言的翻译及其形象的再现》援引数例《红楼梦》原著中王熙凤的语言,从机心、辣手、刚口三方面分析了她复杂的性格。同时结合杨译本中王熙凤的语言的相关翻译,采用纽马克翻译理论做出适当评价,认为杨译以“语义翻译”为主,兼顾“交际翻译”,成功地再现了王熙凤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
(10)《评〈红楼梦〉杨译本中王熙凤形象的重塑》从杨译《红楼梦》的选词、句子结构以及翻译的叙事角度对译本进行分析,发现译文中王熙凤泼辣、粗俗、直率的鲜明个性减色不少,认为杨译本对王熙凤这一典型形象的重塑有所欠缺。
(11)《从文学文体视角看林黛玉形象在翻译中的再现》通过从文学文体角度对《红楼梦》两种英译本四处实例进行对比,认为从文体效果上看,杨、霍两译本在塑造林黛玉这一形象中都有得失。
由文章观之,有关《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英译研究历时不长,若从2007年算起,只有几年。在2007—2015年八年间可以说刚刚起步,研究基本处于零散状态,远未成系统。
2.专著情况
就笔者收集资料来看,有关《红楼梦》英译专著,迄今国内共出版16部,其中港台3部,大陆13部,分别是:《〈红楼梦〉西游记》[15],《〈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16],《〈红楼梦〉管窥》[17],《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18],《霍译红楼梦回目人名翻译研究》[19],《〈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20],《〈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21],《〈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22],《文化可译性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研究》[23],《文化视域及翻译策略:〈红楼梦〉译本的多维研究》[24],《〈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25],《〈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26]。
上述16部专著中,除了《〈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中收录了刘泽权、朱虹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即《英译刘姥姥形象的对比研究——以话语的人际功能分析为例》(收入该书时题目有改动)与人物形象翻译有关外,其余均未涉及《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翻译,更遑论人物形象翻译专项研究。
3.硕博论文情况
有关《红楼梦》人物形象显化翻译的硕士论文尚未查到,笔者只收集到6篇与人物形象翻译有联系的硕士论文,即《〈红楼梦〉人物描写及其翻译中的隐含的语用分析》[27]《从语境对等论〈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王熙凤的性格塑造》[28]《〈红楼梦〉中个性化人物语言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29]《美的传达——论〈红楼梦〉杨译本中的人物外貌描写》[30]《跨文化视角的〈红楼梦〉中涉及人物塑造的隐喻研究》[31]《霍克斯〈红楼梦〉人物话语翻译艺术研究》[32]。
以下是上述6篇学位论文具体介绍:
(1)《〈红楼梦〉人物描写及其翻译中的隐含的语用分析》摘选了《红楼梦》人物描写的一些典型片段作为例子,在对每个例子进行个案分析后把所得到的有关其语用隐含的论证应用于评论部分现有译文的得失,通过从语用学研究所囊括的语境、预设、会话隐含、话语行为等各个研究角度对案例中某些典型隐含进行分析。该文对有关译文的评论重点在于两个方面:①译者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了有关隐含的语用意义;②原文中语用隐含的模糊性在多大程度上在译文中得以传达。
(2)《从语境对等论〈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王熙凤的性格塑造》以哈蒂姆和梅森基于篇章语言学研究的交际翻译论作为理论框架,通过对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中对王熙凤的性格塑造的译例进行对比与分析,从在译文中重建语境对等的角度,探讨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由此导致的两个译本在王熙凤性格塑造方面的不同的翻译效果。
(3)《〈红楼梦〉中个性化人物语言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以杨宪益、戴乃迭译文和霍克斯译文为文本,以小说文体分析为基础,对两个英译本主人公对话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分析人物对话风格传达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影响,评价对话译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认为:《红楼梦》的上述两个英译本在不同的文体类型翻译中各有千秋,基本实现了译文人物语言韵味、风格的传达。
(4)《美的传达——论〈红楼梦〉杨译本中的人物外貌描写》以《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文本中有关人物外貌描写的翻译,聚焦于杨译本中对相应描写的翻译,以服饰、肖像为经纬,对典型译例进行分析评价。对服饰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服饰颜色和服饰材质及款式上,对人物肖像的翻译研究则集中在小说的三个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和王熙凤的肖像描写上。通过对以上相关翻译段落的评析,总结出杨译本所体现出的一些突出特点:杨译本对文化内涵深刻的意象持完全保留的态度,尽力在译作中保持文化信息的原貌;而对于文化印记较淡的表达,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译法,以能让译入语读者获得同样的审美感受为第一要务。
(5)《跨文化视角的〈红楼梦〉中涉及人物塑造的隐喻研究》选用《红楼梦》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的英译本作为研究的主要语料,对比英汉涉及人物塑造的隐喻的异同。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翻译方法划分为的六个不同等级,随机选取了《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前八十回中212个涉及人物塑造的隐喻,对它们进行分组归类,进而对各个类别组的翻译等级做了统计,考察了两译本中体现出来的英汉隐喻的相似性与相异性。
(6)《霍克斯〈红楼梦〉人物话语翻译艺术研究》通过对霍克斯人物话语翻译艺术的分析,认为霍克斯通过在语言各个层面的操控,促使译文中的人物话语比原文中的人物话语更具个性特色,虽然这样做在语言层面违背了原文,但却通过话语成功传达了人物个性,所以广义上做到了对于原文的忠实。
另外,就博士论文而言,笔者遗憾地发现相关研究几乎无处寻觅。但值得一提的是,博士论文《〈红楼梦〉拟声词及其英译研究》在第四章第一小节“揭示人物性格”中单独辟出一个标题来探讨人物形象话题[33],但只从拟声词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就硕博论文情况而言,《红楼梦》的人物形象英译研究,在研究《红楼梦》的硕博论文中有过零星论述。这些论著中的零星成果,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虽然这类零星成果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系统,讨论也不够深入。
4.国外研究情况[34]
西方对我国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的关注由来已久。据资料显示,英美红学始于184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又译郭实猎)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红楼梦》[35]。该文主要将原著故事梗概介绍给西方读者。从19世纪中叶迄今研究势头日趋强劲,现已有西方红学、欧美红学、英美红学(姜其煌语)或英语红学(葛锐语)等不同称谓。
总体而论,西方红学的成长深受国内红学发展影响,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总体上来看,比起《红楼梦》英译,西方学者似乎对原著更感兴趣。有关西方红学研究对象及热点,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红楼梦》里的哲学思想;传统评点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性别、性和女性研究;叙事结构和技巧;虚构型作品《红楼梦》;情;人物研究和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清代续书;还有一些非主流特殊话题诸如表亲婚姻、饮食文化和园林美学”[36],而有关《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的讨论很少见到。
笔者利用 ProQuest 学位论文库提供的资源[37],分别输入 Hong lou meng、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he Story of the Stone、zhonghui novels、Chinese classical/vernacular novels等关键词后搜索出国外与《红楼梦》相关学位论文仅1篇与本书研究有关联,具体内容如下。
黄国彬(Laurence Wong)博士论文[38]——《红楼梦文学翻译研究——以大卫·霍克斯英译本为中心》(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u Me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uid Hawkes's English Version),以英、法、德、意四种语言译就的11种《红楼梦》译本为讨论霍译本的参照对象,通过分析原作个性化语言(idiolect)、方言(dialect)、语域(register)和风格(style)等文学特色在这11个译本中的体现情况,其中第三章“个性化语言”和第四章“方言”及第五章“语域”提到《红楼梦》众多人物如刘姥姥、李贵、冯紫英、马道婆、张太医、北静王、史湘云、贾元春、贾政、贾雨村、甄士隐、贾宝玉、蒋玉菡、秦钟、贾母、薛蟠、焦大、林黛玉、王夫人、茗烟等个性化语言的翻译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重要性。
但是,黄文仅限于呈现翻译现象,而未就其展开深入探究,譬如人物形象采用何种方法译出、人物形象译出是否体现原著特征等。
可见,令人遗憾的是,《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问题迄今没有深入研究资料面世,对于英译人物形象的关注远远滞后于《红楼梦》英译研究中其他领域探究。
综合国内外文章、专著、学位论文所述,目前的《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研究当中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者采用“感悟式”和“印象式”分析方法,绝大多数研究以定性为主。只是在近年来开始有文章将语料库介入相关研究[39],为《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研究提供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可能性。
(2)有关《红楼梦》人物形象英译研究仍然处于零散状态,相应专著迄今空白,对于英译《红楼梦》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缺乏研究,对霍译本中出现的大量“增义显形”现象迄今尚未纳入研究视野。
(3)从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被介绍到国内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国内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从介绍综述到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快速发展。平行语料库建设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红楼梦》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大多就《红楼梦》的语言表述、文化现象翻译等对一个或几个译本进行研究,包括叙事标记语英译[40]、译者风格[41],也有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分析《红楼梦》人物话语和人物塑造[42],而从显化翻译视角研究《红楼梦》人物形象的鲜有涉及,《红楼梦》人物形象翻译是红学研究中尚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红楼梦》的中英文版本研究
版本是翻译研究的基础,正如欧阳健指出的那样:“版本乃红学之本,关系到千百万读者以哪个本子为《红楼梦》的真本,作为阅读、鉴赏、研究对象的大问题。”[43]
“《红楼梦》的创作,经历了‘增删五次’的过程,有人认为这五次增删,都可能有各自的版本流传于世。而它的流传情况,又增加了其复杂性。《红楼梦》的最后一次定稿,完成于乾隆庚辰年(1760),而书的付梓,却是在乾隆辛亥年(1791)。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以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作者的增删,抄手的讹误,后人的校改,使它的版本现象变得极为错综复杂。”[44]
关于《红楼梦》的中文版本,根据冯其庸、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45]所载,就有146种(其中包括一些未见版本)。
《红楼梦》中文版本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八十回抄本系统,因为大多带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所以习惯上称为脂本系统;二是一百二十回刊印本系统,最早由程伟元、高鹗整理刊印,所以又称程高本或程本系统。
抄本系统包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列宁格勒藏本(列藏本)、有正本(戚序本)、蒙府本、南图本、靖藏本、甲辰本(又称“梦序本”)、梦稿本(又名“杨藏本”)、己酉本(舒序本)、郑藏本等。
印本系统包括程甲本、霍底本、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三让堂本、王希廉评本、妙复轩评本、王姚合评本、王张姚评本、王蝶合评本、中华索隐本、亚东初排本、亚东重排本、商务本、世界本、开明洁本、作家本、人民文学本、艺术研究院新校本、浙江文艺本、江苏古籍本、齐鲁本等。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具有恒久的魅力,它在中国文化里产生、流传,在异域文化里也得到传播,这主要是通过它的译文得以实现的。
《红楼梦》在风行海内的同时,很快流传到海外各地。“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便走出国门,传入日本,这时,距程甲本的印刊只有一年多。19世纪,有了英、日、俄文的摘译本和英文节译本。到20世纪,陆续有了日文、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缅甸文、朝鲜文、越南文、蒙古文等世界上主要语言文字的全译本,以及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泰国文的节译本。”[46]
《红楼梦》历经160多年,产生27种外文语言的83个外文译本,仅英译本就有19种之多。[47]
据《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记述[48],《红楼梦》英译史如下:
(1)《红楼梦》的英译发端于1830年以英汉对照方式发表的第三回中“西江月”词二首,译者是英国人J.F.Davis。从那以后,在报纸杂志上陆续出现《红楼梦》片段英译,如 E.C.Bowra 译前八回(1868—1869)。(摘译)
(2)1846年,收入各种选集的有R.Thom所译《红楼梦》第六回的部分片段译文。(摘译)
(3)1864—1869年,E.C.Bowra摘译《红楼梦》第八回。(摘译)
(4)1885年,H.A.Giles译《红楼梦:述宝玉的故事》。(摘译)
(5)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的由H.B.Joly所译《红楼梦》一至五十六回(上册,1892年;下册,1893年)。(节译)
(6)1927年,王良志的节译本《红楼梦》分九十五章在纽约出版。(节译)
(7)1928年,E.Hudson译第四回,名为“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主人公为宝玉。(摘译)
(8)1929年,王际真的节译本《红楼梦》分五十九章出版,次版分六十章在1958年出版。(节译)
(9)1933年,袁家骅、石明的节译本《红楼梦:断鸿零雁记选》(中英对照)出版。(摘译)
(10)1946年,高克毅所译《刘姥姥》。(摘译)
(11)1958年,F.McHugh和I.McHugh姐妹根据F.Kuhn的德文译本转译的围绕宝、黛、钗三个人物的剪辑故事,分五十章出版。(节译)
(12)1964年,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第七十四回至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七回。(节译)
(13)1965年,Ch'u Chai 和 Winberg Chai所译《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节译)
(14)1968年,英国传教士神父班索尔翻译但未出版的《红楼梦》全译本[49]。
(15)1972年,C.Birch所译《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至第六十九回。(节译)
(16)1973年,张心沧以“葬花”为题译第二十三回。(节译)
(17)1991年,黄新渠出版了他的缩写译本《〈红楼梦〉:一个中国贵族家庭的长篇故事》。(节译)
(18)《红楼梦》的全译本由David Hawkes与John Minford的合译本(1973年),共五卷,总书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The Penguin Group)出版。Hawkes 翻译了前三卷,包含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又指导其女婿John Minford翻译了后两卷,包含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第一卷名为 The Golden Days(1973年);第二卷名为The Crab-Flower Club(1977年);第三卷名为The Warning Voice (1980年);第四卷名为 The Debt of Tears(1982年);第五卷名为 The Dreamer Wakes(1986年)。(全译)
(19)1978年,杨宪益、戴乃迭伉俪的合译本,译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共三卷,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全译)
除了以上的19种正式出版的译本以外,还有未经面世的译本值得一提:传说中的 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译本,新西兰人 Edward T.C.Werner(魏纳)曾于1927年发表论文,比较此译本和乔利译本[50],但这一译本始终未曾正式出版。吴世昌先生在《红楼梦探源》的附录《〈红楼梦〉西文译本和论著》中也指出,由于该译本未曾出版,因此未将其列入书目。[51]
(三)对《红楼梦》英译本及其底本的选择与语料库的建立
《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英文全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出版,“不论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或是译事的发展上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52],其问世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译《红楼梦》由企鹅出版公司出版后,“顿时成为经典译著”[53],受到了学者的一致赞叹。
1980年霍克斯《石头记》第三卷《哀世之音》出版之时,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评论道:“《红楼梦》这一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在霍克斯的英译本中得到了完美的艺术再现。这部译者全身心译介的作品流畅生动,是一部真正的杰作。”[54]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uiew of Books)赞誉霍译为“一部光彩夺目、生动逼真的杰作……无愧于原作的深刻”[55]。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世界首席翻译家之一,他评介霍克斯的《石头记》“没有辜负几乎来自各个大洲的汉学家、评论家和读者的期望。他的译文权威、精湛、优美……完全胜任把中国这部18世纪的伟大世情小说的方方面面向英语世界读者传达的任务”[56],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获得接近阅读原著的享受”[57]。
许国璋对霍克斯翻译《红楼梦》评价道:“我觉得最可重视之点,在于他注意到文化情境之移植,使西方读者不仅读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一部中国小说,而且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领略其中风光与人物。其翻译贴切处,为近时兴起的社会语言学提供了最好的例证。”[58]
戴乃迭,作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最早全译本的完成者之一及牛津大学汉学科学士学位的第一位获得者,于1980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发表书评高度评价霍克斯《石头记》前八十回译文。书评从三个大方面肯定了霍译本的独特与价值所在。认为:首先,在版本处理上明智、合理;其次,在丫鬟姓名意译处理上对西方读者帮助巨大;最后,摒弃注脚,通过增译原文来使引用或典故清楚明白,也有助于霍译本再现原文的文学风味。故而,最终评价道:“霍克斯的伟大成就在于以优美的英文使得这部中国名著能够为西方读者所阅读”,并认为自己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与之相比恐怕只能是提供语言学习的直译本。[59]
其实与霍译本几乎同时代出现的全译本,即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称为“杨译本”和“霍译本”的这两个全译本可谓各有千秋,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本书的研究译本只采用由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原因如下: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写,后四十回是由高鹗等人续写;相似的是,对于《红楼梦》的英语翻译,前八十回由霍克斯本人亲自完成,后四十回由闵福德在霍克斯的指导下完成的,考虑到原著作者的创作和译者的翻译的一致性,本书的研究译本采用由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以力求中英文研究语料的典型性和对应性的完整。
本书的对比译本采用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原因如下:
由于这两个全译本均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以译本比较方面的研究亦多为共时性的。杨氏夫妇是译著等身的杰出翻译家,曹雪芹原著所融合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杨氏译本中得到了较为忠实的再现。杨译本在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保存了源语文化特色。Baker认为两个类比语料库“必须涵盖相似的领域、采用相同的语言、有着相似的时间跨度并具有可比的文字长度”[60]。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刚好满足上述条件,因此,两种译本具有很强的对比性。
在选定了进行比较研究的译本之后,就需要确定译本使用的底本。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的底本至少在文字上是固定不变的,尽管其意义可能因人而异。然而,《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却存在诸多不同中文版本,因此译者在建立语料库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译本底本的选择。而要对《红楼梦》的译本进行研究,了解和确定译者当时所根据的底本无疑成为研究工作的首要步骤。因为如果没有确定译者所遵循的底本,那么对译本的评论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译者的评价也必失之公允。
首先,关于《红楼梦》霍译底本,学界众说纷纭。
Hawkes自己在“导言”中说:
It is somewhat surprising fact that the most popular book in the who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mained unpublished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after its author's death,and exists in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none of which can be pointed to as definitely“correct”.(Hawkes,1973:15)
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这部小说竟然在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行,并且还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绝对“正确”,这多少令人吃惊。(笔者自译)
即使在霍译《红楼梦》第一卷“序言”部分,霍克斯自己就底本所做的两处简短说明已经显示前后不一:
a.This translation,though occasionally following the text of one or other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first eighty chapters,will nevertheless be a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120 chapters of the Gao E edition.[61]
本书所译前八十回虽然间或参照这个或那个抄本,但是整本翻译还是以高鹗一百二十回本为底本。(笔者自译)
b.In translating this novel I have felt unable to stick faithfully to any single text.I have mainly followed Gao E's vers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as being more consistent,though less interesting,than the other ones; but I have frequently followed a manuscript reading in subsequent chapters,and in a few,rare instances I have made small emendations of my own.[62]
翻译这本小说,我感觉根本无法忠实参照某个单一版本。比起别的版本来,高鹗底本虽然不太有趣,但由于前后更为一致,故在第一章翻译中我主要还是以这个本子作为蓝本,在其后章节翻译中,我不断参照抄本,有时还自己做一些小修订。(笔者自译)
在上述两处引文中,高鹗底本在霍克斯《红楼梦》翻译中的参照比重实际上自相矛盾。如果根据a,高鹗底本为主要参照蓝本;而如果依据b,高鹗底本只在第一回作为主要参照蓝本,而整部书所参照底本应该是一个百衲本,且经过译者加工的本子。因此,目前译界对于霍译底本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霍译底本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底本,如王宏印在《试论霍译〈红楼梦〉体制之更易于独创》[63]中对霍克斯上述言语做了如下阐释:
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霍克斯第一卷“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64],其中不仅讲了他所谓《石头记》的译本,实际上是一个译者参考众多资料经过重构而产生的一个理想译本的底本,而且说明译者的翻译宗旨,是尽可能传译出这部未完成的艺术杰作中的一切思想的和艺术的东西。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霍译本参照底本的复杂性,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寻根究底。如范圣宇在其专著《〈红楼梦〉管窥》中认为:
要准确无误地指出霍克斯在翻译时究竟哪一段参照了哪一种底本似乎不太可能,也没这个必要,因为如果底本文字相同,探讨他究竟是依据哪种底本显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底本文字有出入,以英文翻译为准则就可以知道他参考的是哪一种底本了。[65]
第三种观点是在学界占主流的观点,认为霍译本主要参照底本为程本。
姜其煌在《〈红楼梦〉霍克斯英文全译本》一文中明确写道:《红楼梦》霍克斯英文八十回全译本,主要根据程高本译出。[66]
洪涛认为,“既然已知道霍克斯是以程本为主,那么,他多据程本来翻译,这是不言而喻的事”[67]。
从霍克斯的翻译笔记看,我们知道他主要的翻译底本是以程本为底本整理出来的“旧行本”[68]。在注释中洪涛对“旧行本”做了解释:
“旧行本”指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按照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的“凡例”,这个本子简称为“旧行本”(相对于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校本”而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霍克斯本人谈到翻译底本时说:
最初以最通用的120回本为底本,当脂砚斋评批本提供了更好的文字时就依脂本。[69]
但后来我才开始对本子之间的差异等问题感兴趣,原因是你开始认真工作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不一致、情节的混乱、本子之间的差异,等等,都冒出来了,当然,那些书和资料也都是逐渐出版的,我很迟才得到那个乾隆抄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没怎么考虑版本问题,开始的时候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和俞平伯的80回校本,后来书才慢慢多了。[70]
1998年访谈中霍克斯提到版本问题时谈得最清楚:
我开始时没有太考虑版本问题,我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四卷本)着手翻译,但那时手中也有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71]
可见,霍克斯翻译中依从最多或者叫作翻译底本的就是人民文学的四卷本即霍克斯所谓的高(鹗)本,参阅最多的是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即霍克斯所谓的脂本或抄本。这一点弟子兼女婿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译者闵福德说得更为清楚:
霍克斯的书架上当然有俞平伯八十回校本,甲戎、庚辰本,和新近抄本的程高影印本,但他工作的脚本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启功注释的四卷本。他做过记号的书目前还保存在岭南大学的图书馆。[72]
笔者查了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本子,从“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这一章节中,找到了此版本的底本说明:“本书整理,系以程伟元乾隆壬子(1792)活字本(校记中简称‘乙’本)作底本”[73],说明霍克斯翻译时所依据的这个人民本大致就是程乙本。在霍克斯英译笔记中前半部分多以人民本称之,后半部分多称为程本。
综上,在创建霍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时,本书可以选取《红楼梦》“旧行本”,即曹雪芹、高鹗所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红楼梦》,即程乙本,作为底本对应。令笔者欣喜的是,由企鹅出版集团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的霍译本[74]已然面世,这为创建霍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提供了便利。
其次,关于《红楼梦》杨译本底本。
根据杨译本“出版说明”,其有关参照底本有下面一段文字:
Our first eighty chapt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photostat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Peking,in September 1973 according to a lithographicedition printed by the Yu-cheng Press,Shanghai,in about 1911.This Yu-cheng edition hadbeen made from a manuscript copy kept by Chi Liao-sheng of the Chienlung era.The lastforty chapters are based on the 120-chapter edition reprint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Peking,in 1959 from the movable-type edition of 1792.The ChiLiaosheng manuscript of the first eighty chapter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pies extant.In our translation certain minor errors and omissions made by the man who copie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have been corrected according to other versions.[75]
参照译文如下:
我们的译本前八十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影印本,这一影印本的原本是1911年左右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该石印本是乾隆年间戚蓼生保存下来的一种抄本。后四十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校勘重印的1792年一百二十回活字印刷本。戚蓼生保留的前八十回手抄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之一。在翻译中,我们参照其他版本,修订了抄本中的错误。[76]
大中华文库《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前言”中也有类似文字说明:
本译本为一百二十回,其中前八十回以“戚蓼生序本”有正大字本为底本,后四十回则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印行的“霍底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对个别地方作了校改或补正。[77]
依据上述出版说明,杨译本所参照的中文底本前八十回参照“有正本”,即戚序本,后四十回则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勘重印的程乙本。
但作为杨译本审校的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以《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论〈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说明”》为题撰文,批驳《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刊登的报道中将杨译本底本说成是“有正本”和“程乙本”的观点:
……译者明明告诉新华社记者说,他们根据北大图书馆的“脂京本”[78]译出前八十回,而出版社却偏偏说是用“有正本”的复制本译出前八十回。译者明明说,后四十回是据“程甲本”译出,而出版社偏偏说是据“程乙本”。[79]
该文中他依据自己审校结果,认定杨译本参校的是“脂京本”(“庚辰本”)和“程甲本”。
12年后,这一观点得到呼应:
英文120回《红楼梦》全译本,可以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及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先生的合译本为代表。此译本前八十回据庚辰本译出,后四十回据程甲本译出,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80]
21世纪初,洪涛在《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中屡屡发现“张冠李戴”以及原文与译文之间无法对应的现象后,再次对杨译本中文底本提出质疑,并依据文字校对推测杨译本有可能根据“庚辰本”来翻译:
查戚序本中无“蚩尤”,亦无“刘庭芝”,庚辰本等抄本却有。杨氏夫妇应该是根据有“蚩尤” “刘庭芝”的本子来翻译的。[81]
但洪涛又认为,第九回金荣的那段秽语在“庚辰本”中被保留,而在号称“洁本”的“戚序本”中却被删,且杨译文并未译出,据此看来译者此处又是依据“戚序本”来译的。
有关杨译本底本的“有正本”和“庚辰本”之争,范圣宇就回目的翻译判断杨译本所参照的底本应当是有正本而非庚辰本。
所以,更可能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出了差错,而“出版说明”则是对的。[82]
另外,在《〈红楼梦〉管窥》脚注中,范圣宇就杨译底本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关于杨宪益小说使用的底本究竟是哪个本子,杨先生自己的说法就不甚一致。如上所述,他在英译本“出版说明”里说的是有正本;但在《银翘集》[83]中却说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在他的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中,他说的是吴世昌先生帮助他与戴乃迭参照了多种手抄本和印刷本,择善而从,编成翻译的本子,这样看来他的译本又是一个“百衲本”了。综合这几种说法,并仔细校读译本,笔者认为它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有正本,并主要参照庚辰本对其中的讹误做了校正。也就是说“出版说明”的说法是准确的。[84]
语料库整体的设计和语料的汇集对于“基于该语料库的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85]。它直接影响到语料库所设计的研究目标能不能有效实现。
霍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创建步骤:
第一步:语料的采集。
语料的采集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光电扫描或键盘输入制作电子文本;二是利用网络上已有的电子文本,并将其转化为所需的格式。由于目前网上《红楼梦》霍底本[86]有现成文本文档,本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采用后一种方式,这样不仅避免简单的重复劳动,又可以降低语料库的建设成本,提高效率。霍译本电子版是扫描并校对得出[87],并且依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的《红楼梦》霍译本进行核对。
第二步:语料的格式化。
除了语料质量,还应保持语料库中语料存储的规范性。从网上采集的原始语料需加工为统一的格式后才能进入到语料库中。为了保持语料的纯洁性,将各种语料统一转化为纯文本(text)格式,即以“.txt”文件的形式存储,以借助 text 文档中不含任何页面显示标记的特点避免“脏字符”对语料内容的干扰。
第三步:相关语料提取。
利用汉字分割软件(ICTCLAS 2008)和语料检索软件(WORD SMITH 6.0.0),提取相关语料并建立平行语料库。
杨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与霍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创建步骤类似,但在第一步“语料的采集”上,由于没有可供编辑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中文Word文档,将程乙本第一回至第八十回与纸质版《红楼梦》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本中的中文进行逐一对照核查,包括标点符号、段落划分和空行等文本特征,将核对结果输入电脑,建立了可供编辑的杨译底本电子文档。
至于语料格式化和语料提取方法与霍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创建相仿,此处不赘述。
二 显化翻译研究综述
(一)翻译共性与显化假说
目前,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翻译共性”的研究。所谓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亦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是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源语语言或目标语原创语言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语言特征,指“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88]。Mauranen等指出,Baker所著《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意义与应用》一文确立了“语言学翻译共性思想在翻译研究核心中的一席之地”[89]。
Chesterman[90]将翻译共性划分为两大类:源语型翻译共性(S-universals)和目标语型翻译共性(T-universals)。前者是基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关注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方式。后者是关于目标语中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之间的关系,重点放在译者对目标语语言的处理方式上。柯飞所提出的“翻译共性”则属于前者,是指“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91]。Baker所谓的“翻译普遍特征”属于后一类,她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而不是源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92],即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目标语原创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特征。这一定义有两重含义:第一,翻译共性是特定语言模式的概率性分布特征,主要在归纳的基础上获得;第二,翻译共性由翻译过程本身造成,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无关。
Baker在前人[93]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普遍特征(universal features of translation)的假设,包括六个方面:(1)译文显化程度显著提高;(2)译文中消歧和简化;(3)合乎译文语法性;(4)通过省译和词汇重设避免重复源语词汇;(5)超额再现目标语语言特征;(6)某些语言特征在译文中表现出特定的分布类型。[94]就翻译共性种类而言,Baker明确提出至少四种可能构成翻译普遍性假说的特征:显化(explicitation)、简单化(simplifieation)、规范化(normalization)、整齐化(leveling-out)。[95]简而言之,Baker提出的翻译共性具体包括:显化、消歧和简化、合乎语法性、避免重复、凸显目标语语言特征及其分布六个方面。相关的实证讨论又增加了传统化、标准化、范化、净化等讨论,后来主要集中在显化、简化和范化三个方面,近年来又增加了独特项假设、干扰、非典型搭配、不对称假设等。这些分别以不同语对或语种的语料库为基础,以语际对比或语内类比为模式的实证研究,既有对原有假设的支持,又有不同程度的背离,引起研究者对现有研究的反思。2001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EST大会和在芬兰萨翁林纳举行的关于翻译共性研究的大会上,与会者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96]
显化假说被纳入翻译共性研究范围内,成为该家族中的重要一员。“虽然显化研究开展时间不长,却是目前翻译领域中得到最为全面研究的现象之一。”[97]
“显化”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学者Vinay与Darbelnet从对法语和英语进行文体对比研究角度提出的。它作为“一种文体翻译技巧”,指“在目标语中对原语中隐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加以明确说明的过程”[98]。Nida 和 Taber指出,好的译文往往会比原文长,主要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通过明示原文中的隐含信息,在一定限度内增加译文的冗余度。[99]
对显化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Blum-Kulka。她于1986年提出了著名的“显性假说”,即“译者对原文的解释过程可能导致译文比原文冗长。这一冗长现象表现为译者提高了译文在衔接层次上的显化程度”[100]。在她看来,显化现象的产生绝大部分是由翻译过程对原文的阐释造成的,即翻译过程本身固有的特征,而不取决于不同语言对(Language pair)的具体差异(如语法体系差异、文体偏好差别)。
Baker最初对于显化做了这样的论述:“相对于特定原语文本以及原创文本总体而言,翻译文本显化程度显著提高”[101]。随后她又指出:“在翻译中,(译者)总体上往往会将各种情况加以详细说明而不是将含糊不清的地方保留下来。”[102]
Séguinot认为,显化不仅仅指原作中不存在而译作中添加的表述,也包括仅在原文中暗示或只有通过预设才能认识到的信息在译文中加以明示,还包括原文中的某些成分在译文中通过凸显、强调或词汇选择等手段而加以突出的现象。[103]
贺显斌认为,只要译文中的词句意义比原文更清楚、明确、具体、易懂,逻辑关系比原文更明晰,或中心意思比原文更突出,就算发生了明晰化转换。[104]
柯飞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翻译现象,显化(以及隐化)不应只是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应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在译文中添加了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105]
Pym也对Blum-Kulka的“显性假说”发表过类似看法。他认为,首先,该假说只局限在语篇衔接层次,从严格意义上讲未涉及所有语篇或语篇部分以外的语言使用,更不用说涉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其次,该假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的只是译本语篇衔接标记的不必要重复,而不是信息从隐化变成显化的完整过程。[106]
匈牙利学者Klaudy等对显化类型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分类,提出了强制性(Obligatory)、选择性(Optional)、语用性(Pragmatic)、翻译本身固有(Translation-inherent)四种显化类型。[107]其中,“强制性显化”由不同语言在形态、句法、语义方面的差异所致,如从俄语翻译成匈牙利语时必须加冠词,而相反方向要省略冠词。“选择性显化”依赖语言的使用,取决于目标语文本的不同文体取向,即“为了创造出语法正确、自然、近似本族语的句子,译者可能选择使用更为显化的表达方式”[108]。以上两种显化类型,都涉及目标语中插入语言成分。“语用性显化”由文化差异所致,为了跨越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鸿沟,译者往往要在译文中加以解释说明。例如,译语读者可能对源语读者熟知的文化概念或地理名词一无所知,因此译者需要在译文中明确该概念或名称。而“翻译本身固有显化”既“不取决于源语与译语间结构、形式或文体方面的差异,也不受制于具体文化特征的语篇成分,而是由翻译过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109]。具体来讲,目标语对源语中的思想和想法进行二次加工和整理过程可能会影响译文的长度,因为译者要遵循不同于源语的思考方式,采取更为复杂的认知途径。
显化研究从对比模式上也可分两类:一类是指翻译过程中在译文中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implicit)语言成分的过程,目的在于更清楚地传达原文中的语法和非语法信息;另一类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译语中非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显性程度(explicitness)提高。前一种显化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语际对比基础上的显化,简称语际显化(inter-language explicitation);而后一种显化是目标语内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比较所表现出的语内类比显化,简称类比显化(comparable explicitation),此二者都应作为显化研究的对象。
显化研究从影响因素方面,又可分为强制性和选择性两种,前者是语言系统影响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译者、翻译过程、目标语规范等多种因素。而从译者角度,又分为有意识的策略和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
黄立波和王克非认为,汉英/英汉翻译中的显化可做出分类(如表0-2)。[110]
表0-2 显化的分类

注:语内对比也称为类比。T1=翻译汉语;T2=原创汉语;Cst=汉语原文;Ett=英语译文;Est=英语原文;Ctt=汉语译文。“强制性”显化=语言系统差异导致的显化;“非强制性”显化=翻译过程导致的显化。
(二)前语料库时期的翻译显化研究
因为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传承,笔者参照Laviosa[111]和Olohan[112]的做法,以Baker[113]的“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一文为界,将翻译共性研究划分为前语料库(pre-corpus)和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两个时期加以评述。
前语料库时期的翻译显化研究,主要是从语际对比的角度出发;而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下,翻译显化研究呈现出多样化,既有语内类比基础上的研究,又有以语际对比为模式的研究。
这里所谓“前语料库时期”就是指大规模机读翻译文本用于翻译研究之前,通过人工采集原文与译文文本,并对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行人工对比、分析和统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共性研究主要表现为从词汇、句法和文体等语际对比的角度关注显化问题。
在语料库翻译方法提出之前,有关显化的研究主要有Vinay 和 Darbelnet、Nida 和 Taber、Vanderauwera、Blum-Kulka、Klaudy等。
Vinay 和 Darbelnet[114]是从对比文体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的,他们将显化和隐化视为一组对立的文体翻译技巧,常与信息的获得和损失相联系。所涉及的显化包括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两种,这两种显化表面上都是语境或情境要求的结果,但从本质上讲依然是语言系统差异造成的,属于强制性显化的范畴。
Nida 和 Taber[115]指出好的译文往往会比原文长,主要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通过明示原文中的含蓄信息在适当限度内增加译文的冗余度。他们主要是从语言文化差异和方便译文接受者理解原作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中的新信息现象。
Vanderauwera[116]指出了译者常用的10种显化策略,这些技巧均不在语言系统差异影响之列,但与译者的个人文体偏好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用语料库研究译者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Blum-Kulka[117]从翻译中衔接与连贯的转换入手提出了显化假设(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这一假设有两个特点:第一,将显化视为翻译过程内在的属性,摆脱了语言系统差异的影响,使显化研究具体化;第二,从句法的非强制性转换入手,将译者的文体偏好作为参数之一。Blum-Kulka的论断为后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Klaudy[118]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内在显化四类,各类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却让我们认识到显化现象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在此基础上能对翻译共性做出更加全面的认识。
前语料库时期的翻译显化研究主要是指在语际对比基础上翻译文本相对于源本文表现出的形式方面的特点,都是Baker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直接或间接的思想来源,研究内容与方法在之后的语料库显化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共同点是关注翻译文本中的规律性语言使用模式。与Baker方法不同的是,这些研究都是以源文本为标准来衡量译文。
相对于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前语料库时期的翻译共性研究表现出以下问题:(1)每个研究都是从不同视角,如对比语言学、文体学或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在对个别概念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2)在关注焦点上,词汇、句法、文体等层面均有涉及,但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3)对共性的研究主要以语际转换为基础,即相对原语而言译语的普遍特征,限于探讨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这种二元对立的做法常常将译文视为原文衍生物,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本质上依然是对译文质量的回溯式评估。
尽管如此,这些前期研究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显化研究
语料库翻译学也是对原有翻译研究范式的传承,所不同的是着眼点和方法。前语料库的研究以“源文本”为中心,采用人工的文本对比方法;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则以“目标文本”为导向,采用计算机数据提取、统计与分析技术,将关注焦点放在翻译语言上。
语料库用于翻译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19]但当时文本采集的规模通常较小,并且多以手工统计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期,平行对齐的语料数据开始应用于机器翻译。Baker的《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120]一文,倡导用语料库方法研究翻译,标志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的诞生。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显化研究打破了前语料库时期研究建立在内省数据基础上演绎式、规定性的规则系统,由规定转向描写,以翻译本体为研究对象,由大规模翻译文本或翻译语言整体入手,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模式,对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的本质。根据Baker[121]等,翻译共性研究目的在于识别翻译文本的典型语言特征,这样不仅可以揭示“第三类语码”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影响翻译行为以及隐藏于此类独特语言形式之下的各种具体的制约因素、压力和动机,从而达到对翻译现象的深层解释。
Baker对显化的最早界定是“与特定源文本或(目标语中)原创文本总体上相比较,(目标文本)所表现出显性程度的显著提高”[122]。从这一界定可看出,Baker当时所讨论的各种翻译共性既有单语内类比(comparable),也有语际对比(inter-lingual)。
单语内类比模式的第一类是对形式词汇或标记的考察,如Olohan 和Baker[123]通过对叙述动词(如say,tell)后选择性“that”在翻译英语语料库(TEC)和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中的频次进行考察,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就此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
Olohan考察的同样是对形式成分的选择性显化,具体切入点包括补语标记词that、关系代词wh-/what、动词补语小句中的to be、that从句中should省略与否等选择性句法成分和词汇成分在翻译文本和目标语非翻译文本中的使用情况。[124]Olohan认为翻译文本中对选择性句法成分的过多使用,目的在于明示各种语法和词汇关系,对选择性词汇,如人称代词的使用频次低,说明译文为了明示语义信息往往会以名词化结构代替原文中的人称代词形式。
Olohan在TEC和BNC的基础上,对英语翻译文学和原创文学中各类缩写形式(contracted forms,如’s,'ll,'d,'ve,'t,'re等)的种类和频次考察发现,翻译文学在两方面均低于非翻译文学,说明翻译文本表现出显化的倾向。[125]
单语内类比模式的第二类是对句法形式的考察。如Puurtinen通过对翻译芬兰语的语言特征以及意识形态规范进行考察发现:非翻译芬兰语作品中非定式结构的出现频次低,而译自英语的翻译作品中,非定式结构的使用频次明显高于当代非翻译芬兰语作品。[126]
胡显耀与王克非[127]利用“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128]考察了翻译汉语区别于汉语原创语料的词汇使用特征。他们发现,无论是文学语料还是非文学语料,与原创汉语相比,翻译汉语具有虚词显化、指代方式显化、常用词频率增加等特征,从原创汉语与翻译汉语对比的角度验证了Baker提出显化假设。
同一时期,以平行对应语料库为基础的语际对比模式从语言转换入手,双向考察语际显化。
语际对比模式第一类主要是从词汇或句法双向转换入手。
Schmied和Schffler以克姆尼茨英—德翻译语料库(Chemnitz)为基础,将英—德翻译中的显化分为结构显化和非结构显化两类,分别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层面。[129]这项研究表明英→德和德→英两个方向上均表现出显化,初步说明显化确是翻译过程的共有特征。Schmied和Schffler继而从认知和信息加工的角度对显化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Øver·as以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ENPC)为基础关注了词汇衔接现象,结果表明从翻译方向上看,总体上英语→挪威语方向上的显化要比挪威语→英语方向上更为突出[130]。这一发现,与Schmied和Schffler的发现不完全一致。Øver ·as的研究表明尽管两个方向上都表现出显化,但程度有差异,说明具体语对是一个重要变量。Øver·a s特别指出,语际显化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类比显化的必要补充,因为翻译文本相对源文本显性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说明翻译文本就比目标语中的同类原创文本显性程度高。这一研究初步将平行与类比两种模式联系了起来。
Perego以两部匈牙利语电影及其意大利语字幕为考察对象,从类别和形式上证实了电影字幕中翻译上存在显化现象。[131]从类别上,显化现象被划分为“文化”(Cultural)、“符号间转化”(Inter-semiotic)、“基于简化需要” (Reduction-based)三类。从形式上,显化现象表现为“添加”(Addition)和“具体化” (Specification)两种。具体来讲,前者指在译文中添加有别于原文中使用的语言学(语法、词汇或句法)成分,后者指用语义更为详尽和明晰的词语替换语义较为笼统和宽泛的词语。
柯飞以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对汉语特殊句式“把”字句在英汉转换中的分布特点进行考察发现:翻译汉语作品中的“把”字句要比非翻译汉语中的“把”字句频次高,文学类作品比非文学类作品频次高,由于“把”字句适于表达复杂和细微的意思,因此“把”字句的频次说明了翻译文本中的显化现象。[132]
语际对比模式第二类研究属于纯形式的对比。
贺显斌对O.Henry的短篇小说The Last Leaf及其汉译文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发现汉译文中显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该倾向具体表现为:在原文全篇134句中,译成汉语后显化程度提高的有79句,占汉译文全篇句子总数的59%。[133]
王克非根据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4个子库(汉译英文学、汉译英非文学、英译汉文学、英译汉非文学)中句对应抽样检索发现,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译本都呈现出字数扩增的现象,而且不同类型的译本在扩增程度上有差别。[134]他认为广义的显化现象可能是导致译本字数扩增的原因之一。
Frankenberg-Gacia以葡—英双向平行语料库(Compara)为基础,以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了翻译文本中词汇数量的整体增加表明译文往往比原文更为明晰,而且这并不受制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135]
Klaudy和Károly在对英译匈和匈译英文学文本两个方向上报告动词(reporting verbs)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显化的“非对称假说” (Asymmetry Hypothesis),[136]指出译者在Ll→L2方向进行了显化处理,在相反方向却并不总会进行隐化处理。通过对从3部(1部英文和2部匈牙利文)小说中随机抽取的各100个报告动词及其匈/英译词进行对比分析,从不同报告动词数与报告动词总数的比率以及仅出现一次的报告动词数与报告动词总数的比率分析后,Klaudy 和 Károly认为“译者更愿意使用显化操作,而不使用选择性隐化操作”[137]。
柯飞通过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语料库中的汉英互译实例进行分析,发现翻译中显化(和隐化)现象的发生由语言、译者、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他认为显化现象“不应只是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应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在译文中增添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138]。
Gumul将同声传译中是否存在显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139]通过分析14位波兰语口译者同声翻译的2篇英语演讲稿的录音及其对自己口译结果的回顾式评论(Retro-speetive Comments),Gumul发现同声传译中也存在显化现象,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现象属于口译者下意识的行为,而并非他们有意采取的策略。
Englund-Dimitrova综合采用“有声思维记录法”(Think Aloud Protoeol)和对译文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显化技巧的使用与译者专业水平有关。[140]专业译者下意识使用显化技巧的程度最高,语言学生往往有意识地采用显化技巧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相对于前两类译者而言,翻译专业学生显化技巧的使用,表现为下意识、有意识兼而有之。
这一时期,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不统一的地方,语际共性与类比共性的讨论兼而有之。此后,单语类比模式与双语平行模式的翻译共性研究同步发展。
另外,也有通过语内类比与语际对比两种途径兼而用之考察显化现象的,如Papai使用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研究文学/非文学文本,从逻辑—视觉关系、词汇—语法、句法、语篇—超语言因素(Extra-linguistic)四个层次综合考察了英译匈显化技巧的具体运用,比较了匈译语与匈非译语中文本显化特征的分布。[141]研究结果证实译文中运用了显化策略,译文中显化程度高于非译文。
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翻译则以“目标文本”为导向,采用计算机数据提取、统计与分析技术,将关注焦点放在翻译语言上。为了区别于前语料库时期的源文本—目标文本的语际对比模式,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翻译发展初期主要采用目标语中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比较的单语内类比模式,在初期以类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为基础建立了目标语单语类比模式,即对比目标语中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文本特征。“在不考虑所涉及源语言或目标语言的情况下,识别翻译文本中的特定语言模式,探索翻译本质。”[142]类比模式的语料库显化研究主要是对Baker所倡导模式的应用和验证。
描写翻译研究是Baker语料库翻译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一研究学派抛开“对等”和源文本,以“规范”(norms)为核心概念,关注目标语文化中的“翻译”事实,并对翻译事实进行客观描写。描写翻译研究跳出“对等”的局限,将关注点放在翻译文本整体尤其是对翻译行为规律性的描写上,而不是关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关系的个案研究或对比分析上;强调建立独立的学科分支、完善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强调翻译行为的概率性,并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同时这一研究过程具有可观察性和可重复性。[143]
总的来说,基于语料库的共性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1)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共时语料为研究对象,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分析数据,如平均句子长度、类符/形符比率、词汇密度等手段对词汇多样性、信息负载度等方面进行考察;(2)以对共性的验证和描写为主,解释较少;(3)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4)主要以单语类比语料库为基础,探究相对于目标语原创文本而言的翻译文本特征。这项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单语类比语料库范式向单、双语结合语料库(包括单语参照库和双语对应库)综合发展的过程,研究内容由词汇向句法、语篇层次延伸,宏观与微观、理论阐述与实证性研究并举。
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翻译研究较少关注译者“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144]。“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共时语料为研究对象,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分析数据,如平均句子长度、形符/类符比率、词项密度等手段对词项多样性、信息负载度等方面进行考察……主要以单语类比语料库为基础,探究相对于目标语原创文本而言的翻译文本特征。”[145]“采纳的多是翻译产品/目标语取向(product/target-oriented)的视角,着重探讨翻译文本相对于非翻译文本而言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146]
尽管Baker所倡导的单语类比模式是翻译描写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在对所描写现象的解释中,源文本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否则就只能说明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有差异而已。
首先,在方法论方面,语料库翻译学的初衷是要建立一套有别于单一源文本—目标文本对等与否的回溯式研究模式,而以目标语文本为取向,将翻译文本整体视为研究对象,考察翻译文本不同于非翻译文本的特征。但实际研究中,源文本不可能完全被忽略掉。例如,Baker对显化的最早界定是“与特定源文本或(目标语中)原创文本总体上相比较,(目标文本)所表现出显性程度的显著提高”[147]。从这一界定可看出,Baker当时所讨论的各种翻译共性既有语际对比,也有语内类比。
Bernardini和Zanettin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共性概念的界定和所采用的方法论两方面。[148]关注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模式就会有差异。在翻译共性研究中存在两种对比模式:(1)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语际对比模式;(2)目标语中译文文本与原创文本的语内类比模式。
之后一些学者[149]建议将含有“源文本”的平行语料库重新引入语料库翻译研究中,作为对类比模式的补充。黄立波、王克非认为:“脱离源语文本而仅对译文做纯形式的语料库统计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意义不大……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来表现源文本中的某些特征。”[150]
黄立波、王克非也认为显化翻译应“在指导原则上,以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在翻译研究中重新引入源语文本”[151]。“脱离源语文本而仅对译文做纯形式的语料库统计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意义不大……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来表现源文本中的某些特征。”[152]
“在方法论方面,单语类比语料库研究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1)排除源语文本而孤立地讨论翻译问题;(2)目标语内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可比性的缺乏……导致研究结果信度与效度的缺乏……基于语料库的普遍性研究需要打破类比语料库研究模式的垄断,重新将源语文本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视野。”[153]
其次,根据Baker[154]等,翻译共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识别翻译文本的典型语言特征,这样不仅可以揭示“第三类语码”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影响翻译行为以及隐藏于此类独特语言形式之下的各种具体的制约因素、压力和动机,从而达到对翻译现象的深层解释。对此,吴昂、黄立波提出了质疑:一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二是对各种变量的关注与控制。[155]以译者因素为例,一方面可就不同译者对同一原作或同一作者作品的翻译加以考察,这种研究属于译者文体或翻译文体学范畴;另一方面则是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即将外语文本翻译成母语,还是将母语译成其他语言,同时涉及翻译方向因素。目前,英译汉文本大多属于译入,即由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完成,而汉译英文本中的情况可以分为汉语母语译者、汉英合作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三类,后两类所占比例较小,这也是影响语料平衡性的一个因素。
Toury提出,对翻译共性的研究既不应过分具体化,也不可层次过高,而应当采用概率思维方式对其加以认识,并以条件式表述方法加以描写和解释;翻译共性研究并非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解释力问题,即如何借助各种概念工具对翻译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156]
三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
1.研究假设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中,曾批评“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的“佳人才子等书”,皆为“通共熟套之旧稿”。而他在《红楼梦》中对人物的塑造,虽传承着民族艺术传统的创作特色,着重于传神的性格刻画和深邃的内心世界的描写,但也并不忽略描写形貌,而是使人物创造的“写形”与“传神”相互照应,特别是对男女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以及王熙凤的典型性格的创造,更是将其容貌特征融合在性格特征的创造里,使之形神兼备、各具风采,令人过目不忘。[157]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的主人公,也是其中三个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显示着不同的个性,反映着各不相同的社会人生意义和美学价值,霍克斯是如何显化翻译这些不朽的艺术典型的性格生命的呢?
黄国彬认为在众多的《红》译本中,“霍克斯的翻译是最出色的,在准确性、想象力和创造力上都超过了其他本子,最值得仔细研究,也包含了更多的翻译技巧”[158],“当之无愧是曹雪芹巨著的好伴侣”[159]。
黄立波和王克非认为,汉英/英汉翻译中的显化可依据不同的语料库类型将显化分为语内对比显化和语际对比显化两类。前者是基于目标语中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的对比研究;后者则是源语与目标语文本比较分析的结果。[160]任何语言类型通常都包括形式和意义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它们又进一步分为形式上和意义上的显化两类。
通常认为,翻译转换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完全是语言系统具体差异的结果,但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161]表明,翻译中的显化在许多情况下确属一种非强制性策略,并非译语文本的绝对要求,即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信息或明示隐含信息,均不是译文语言系统所强制要求的。
本书以黄国彬关于霍译本的观点为假设前提,以黄立波和王克非的显化分类为基础,提出霍克斯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了非强制性显化翻译。
本书充分考虑到语料库设计中的可比性、研究中的参数选择与文体类型选择、翻译方向、译者因素等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的因素,因此,以语料库设计中的可比性、研究中的参数选择与文体类型选择、翻译方向为控制变量,在上述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就译者因素提出如下假设(见表0-3)。
表0-3 霍译本对《红楼梦》人物形象显化的假设

假设1:从语际显化方向上看,霍译本在形式和意义上均突出原著《红楼梦》主人公人物形象。
假设2:从类比显化方向上看,霍译本在形式和意义上均比杨译本突出原著《红楼梦》主人公人物形象。
假设3:霍译的显化翻译乃有意识的策略,而非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即霍克斯对《红楼梦》主人公人物形象进行了非强制性显化翻译。
2.研究检测项
本书的考察语料库是由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对比语料库是由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Hsien-yi Yang 和 Gladys Yang)翻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参照语料库是他们各自的《红楼梦》的原著前八十回。
为了便于表述,下文分别将以上语料库简称为霍底本、霍译本、杨底本、杨译本。
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研究假设与语言层面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以具体的语言检测项为切入点来考察翻译现象。“在实证研究中,如何将高层面的显化概念转化为低层面可供语料库检索的数据,成为基于语料库研究的关键。”[162]
Noel指出,语义本身是不能够直接观察的,而译文是译者对原语中构式A的语义的判断,如果构式A在相当规模的语料库中都译为另一种语言中的构式B,而构式B是明示了某语义 [S] 的,便可以认为构式A也含有语义 [S]。这种证据是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直接证据。[163]据此,笔者认为:其一,若源文本中的人名前后有构式A在霍、杨翻译语料库中都译为构式B,且若霍译语料库中构式B是明示了某语义 [S] 的,则源文本中的人名前后构式A也应该含有此语义,若源文本中的人名前后构式A没有含有此语义 [S],则霍译语料库可视为显化翻译;其二,若霍译语料库构式B是明示了某语义 [S] 的,而杨译语料库构式B没有含有某语义 [S],则霍译语料库可视为显化翻译。
故本书的检测项是源文本中的“人名”和它在霍、杨翻译语料库译文中的对应“人名”,通过寻找“人名”的前后词项确立平行语料库语言之间的对应构式,通过比较对应构式的语义对应程度来考察源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在译文中的显化现象。
3.研究步骤
第一,运用ICTCLAS 对霍、杨底本进行分词处理,并运用 WORDSMITH 6.0.0的CONCORD检索功能,分别对考察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及对比语料库中《红楼梦》人物的出现次数和该词的左右语境词进行初步观察。
第二,利用WORDSMITH 6.0.0的COLLOCATE工具分别为考察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生成Word Cloud搭配词云图,直观地得出“人名”左右的搭配词序列,从这些词中选择拟作为例证的形式,“将搭配序列作为研究单位是必要的策略:搭配序列的异同对比直接指向双语短语单位的对应关系;只有当被比单位的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都相同或相似时,它们才可能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对等”[164]。
第三,选择拟作为例证的形式,主要依据为:在霍底本和霍译本中都高频出现,形式构成特征较为明显,便于深入分析。“平行语料库显示的翻译对等是对比研究切实可行的出发点,而反复出现的翻译对等(recurrent translation equivalent)……揭示了双语词语一个侧面的对等关系,因此是最重要的对比依据。”[165]
第四,根据WORDSMITH 6.0.0提供的搭配词频数,确定考察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典型对等形式,然后再从对比语料库中,找出杨译本的相同序列搭配词,再以搭配序列为研究单位,考察并确定能够展现人物形象的词项。
第五,数据提取。运用WORDSMITH 6.0.0的CONCORD,以上述典型形式为节点词分别从霍底本和霍译本及对比语料库杨译本抽取符合要求的索引行,从平行语料库显示的复现翻译对等出发,考察它们在双向翻译过程中的语义对应关系和互译数据。
第六,分析与讨论。主要包括:根据考察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及对比语料库中的对应数据,分析霍、杨译本对人物形象翻译的策略;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和讨论。
(二)研究方法
语料库是研究的工具,语料库的使用也需要先进的工具,“能使我们简洁、有效地进行编码,能使我们查询并获得大量的数据”[166]。本书运用中国科学院的ICTCLAS汉语词法分析系统和牛津大学出品的WORDSMITH文本处理与分析软件,为语料库在切分、标注、统计等方面提供极大的方便,使研究过程更具直观性,研究结果更具信度与效度。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是近十多年随语料库语言学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分支,包括方法论或工具层面上的应用研究、描写性研究和关于翻译特征的抽象性理论研究。它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语料库翻译学以电子文本为基础以计算机统计为手段,对各类翻译现象进行大范围的或特定范围的描写,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探究两种语言及其转换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或验证关于翻译的种种假说”[167]。
借助语料库开展显化研究,能全面快速检索语料,以实证的手段对各类文本的翻译特征进行定量描写和定性分析。“大规模语料库(包括原文及译文)将为翻译研究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翻译不同于自然生成语言或其他任何文化互动形式的原因。”[168]
语料库翻译学“通过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展示语料库研究方法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连贯、综合、丰富的范式”[169]。
“双语语料库有助于翻译对等的研究”[170],“帮助研究者洞悉翻译的本质”[171]。“使用双语语料库数据分析为译者提供不同语言中可能的翻译单位或者对等篇章单位的集合,提高译者的翻译意识,即对翻译难点的处理意识和对翻译策略的运用意识,有助于改进翻译的终端产品。”[172]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方法至少有两大特点: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和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这一研究模式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语料,从假设出发,在各种语言中不断加以验证和置疑,周而复始,使得研究逐渐深入。Chesterman指出,“一门科学只有通过在单个个案之间寻找其相似性并从中加以归纳,才能达到对未来研究或尚未研究个案的预测,从而取得进步”[173]。
本书对象都是真实使用的文本,本质上都是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具体包括七个步骤[174]:(1)提出假设;(2)设定研究目标;(3)检验假设;(4)分析数据;(5)对发现进行理论阐述;(6)将假设精确化;(7)在前六项基础上为将来的研究提出新假设,研究对象都放在语言的规律性特征上,方法上以文本对比为基本模式。
1.双语平行对比与单语平行类比相结合
Bernardini和Zanettin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中存在两种对比模式:(1)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语际对比模式;(2)目标语中译文文本与原创文本的语内类比模式。[175]
前语料库时期的翻译显化研究主要是从语际对比的角度出发,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显化研究既有单语内类比基础上的研究又有以双语语际对比为模式的研究,但以单语内类比研究为基础的显化研究较集中。在方法论方面,单语内类比研究语料库研究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1)排除源语文本而孤立地讨论翻译问题;(2)目标语内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可比性的缺乏。这些都导致研究结果信度与效度的缺乏。一些实证性研究的结果[176]已经证明,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研究需要打破单语内类比语料库研究模式的垄断,重新将源语文本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视野。国外新近研究已经证明双语语际平行语料库在双语对比和翻译研究中的有效性。[177]本书所采用的汉英/英英平行语料库将双语语际平行模式和单语内类比平行模式结合起来,如图0-1。

图0-1 双语语际平行模式与单语内类比平行模式相结合的对比模式
如图0-1所示,本书所用的语料库包括《红楼梦》霍译底本、《红楼梦》杨译底本、《红楼梦》霍译本及《红楼梦》杨译本四类。其中,A—B和C—D分别为单语平行对应关系;A—C和B—D分别为双语平行对应关系;A—C和B—D方向上的语料之间为对比关系;C—D方向上的语料之间为类比关系。以平行语料A—C和B—D对比翻译中的语际显化过程,以平行语料C—D类比翻译中的译者显化策略和手段的差异,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平行和类比对应关系,既考察中文源语文本和英文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又对比两个英文翻译文本之间的特征,对《红楼梦》霍译本人物形象翻译现象进行三维考察。
2.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语言学领域内每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大都由该学科领域对基本数据看法的改变而引发。”[178]
本书不仅关注单一类比模式(the comparable mode)下霍译文本与杨译文本之间的差异,而且也将源文本作为分析和解释翻译文本中特定人物形象转换现象的一个维度。
本书的研究范式在内容上既包括语际转换中译文相对于原文的语言特征,也包括目标语内部译文文本之间的语言特征。采用的方法包括对比分析、单语类比语料库模式、双语平行语料库模式等。研究性质以实证性描写为主。借助语料库工具,以实证的手段对各类文本的翻译特征进行定量描写和定性分析,遵循“让语料说话”的原则,关注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的“翻译”事实,并对翻译事实进行语料数据的采集和统计等定量研究,强调翻译行为的概率性,将关注点放在翻译文本上,尤其是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翻译行为规律性的描写上,对特定语言形式转换现象的大规模观察与分析,以定量分析的方式揭示了不同译者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翻译的倾向,总结译者的人物形象翻译策略。
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显化翻译理论,对研究对象、语料选择、数据描写做出合理分析和解释,对隐藏在数据表象背后的因素进行定性研究。
3.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本书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描写,但描写的最终目的是对翻译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从可观察的现象入手,对翻译文本进行描写,逐步达到对各类深层关系的认识,并最终达到对无法直接观察的过程的重构,通过描写达到最终对翻译现象的解释。
本书所采用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建立在两块土壤之上: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和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语料库语言学从语言研究角度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理念和方法上的依据,以文本对比为基本模式,从假设检验入手,关注典型的翻译语言模式,注重概率性统计分析。描写翻译研究则是从翻译研究角度提供具体研究对象和理论方面的支持,对真实文本进分析和描写,达到对语言现象的客观认识。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为双语平行对比与单语平行类比描写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先有针对性地进行描写和分析,然后再上升到整体归纳和解释。本书在对显化翻译人物形象的现象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不仅从翻译活动内部尝试在源语文本中寻求对这些发现的解释,更从外部如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等视角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柯飞在考察汉英/英汉翻译中的隐和显时指出:翻译中的隐和显可由语言、译者、社会文化、文本类型等多种因素造成。[179]若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就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对翻译普遍现象的解释机制,加深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
本书将《红楼梦》前八十回霍克斯与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人物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形象的全部语料加以梳理归类,进而从不同的角度摘引出霍译显化所在。通过大量的语料事实证明霍克斯的英译存在着显化的特点,再通过对典型译例的阐释,说明这些显化的翻译策略符合译者对读者的认知考虑,并阐明认知中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文本语境和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对译者的要求。
(三)创新点
1.研究内容创新
自1979年至2012年,国内学者对《红楼梦》英译的研究论文多达782篇。[180]然而,这782篇文章中对人物形象“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章只有七篇”[181]。迄今为止,对《红楼梦》的人物形象英译研究只有过零星论述,虽然这类零星成果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系统性,讨论也不够深入,研究内容针对《红楼梦》主人公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形象翻译的尚不多见。
2.研究方法创新
大规模原文和其对应译文的电子语料库以及相关语料库技术所提供的大规模数据检索与提取为本书从海量的语料存储中获取自己所期望的重要信息提供了新方法。
“《红楼梦》长达一百二十回,多达七十余万字,共描述了四百四十八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客观上讲,研究者面对如此庞大的文本信息量,没有合适的统计工具,单凭手工统计,很难进行全面的数据提取和分析验证,而应用语料库,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182]
正如王宏印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大会总结报告中所说的:“虽然有不少新概念的引入和新方法的使用,但研究方法上还是有一定的束缚和限制。例如定性研究多而定量研究少……”[183]虽然有研究的实例,但感悟式的或点评式的研究居多,没有涵盖所有的相关情况,缺乏系统性,而且取样不完整也不够全面,类似本书从语料库包含的海量语言证据中全面抽取有说服力的研究考察尚不多见。
3.研究模式创新
张美芳指出,“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对一些难以捉摸的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和阐释,能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译者的烙印确实存在”[184]。
本书语料库中的一对多模式,即一个源文本的两个底本分别对应两个译文的模式是一大特色,不仅进行不同翻译方向上跨语际的语言转换对比研究,还进行相同翻译方向上译出文本的类比研究,目前对文学作品领域文本的类似研究模式尚不多见。
4.研究视角创新
从研究视角来看,前人对霍克斯英译的研究,从传统的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开始转向功能对等、目的论和文化研究,即从文化学视角、语言学视角和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研究。但总体来看,语言层面的阐释多、价值判断多,在价值判断层面上仍然囿于忠实和非忠实的标准;对于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的效果,前人的研究中都肯定了他作为译者的创造性,也注意到了中西文化及思维的差异,但却鲜有深究译者创造性翻译的动因,更没有深入研究赞助者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影响。像本书这样涉及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翻译赞助商目的、读者需求等问题的考虑,涉及译者对于作者、译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地位和自身使命的深刻理解,尤其是文化传播如何借助于翻译手段操作层面得以实现的研究尚不多见。
[1]David Hawkes,“The Disillusionment of Precious Jade”,in John Minford & Siu-kit Wong (ed.),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p.268.原文如下:“a book that in some sense epitomizes their whole culture.”
[2]刘梦溪:《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3]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
[4]David Hawkes(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Ⅲ),London:The Penguin Books Ltd.,1973,p.25.
[5]详见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磊荣《文化可译性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邱进、周洪亮《文化视域及翻译策略:〈红楼梦〉译本的多维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可培《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译作的再生》,载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374页。
[6]详见谭载喜《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任东升《语篇翻译与译者的写作》,载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15页;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7]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8]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9]闫敏敏:《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外语教学》2005年第4期。
[10]陈曜:《〈红楼梦〉英译史及其在英语文学中地位初探》,《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1]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中国外语》2012年第1期。
[12]冯其庸:《红楼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期。
[13]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4]魏瑾:《从文学文体视角看林黛玉形象在翻译中的再现》,《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5期。
[15]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
[16]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冯庆华:《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冯庆华:《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19]赵长江:《霍译红楼梦回目人名翻译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0]肖家燕:《〈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22]刘泽权:《〈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3]李磊荣:《文化可译性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4]邱进、周洪亮:《文化视域及翻译策略:〈红楼梦〉译本的多维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严苡丹:《〈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26]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陆梅:《〈红楼梦〉人物描写及其翻译中的隐含的语用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04年。
[28]田婧:《从语境对等论〈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王熙凤的性格塑造》,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年。
[29]徐文臻:《〈红楼梦〉中个性化人物语言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石油大学,2008年。
[30]梁艳:《美的传达——论〈红楼梦〉杨译本中的人物外貌描写》,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
[31]付红丽:《跨文化视角的〈红楼梦〉中涉及人物塑造的隐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32]孙洋:《霍克斯〈红楼梦〉人物话语翻译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
[33]黄生太:《〈红楼梦〉拟声词及其英译研究》,博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第53—75页。
[34]此处“国外”主要涉及英国和美国等西方英语国家。
[35]《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文库》。题为《红楼梦》的那篇文章,英文名称是“Hung Lou Meng”,或“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
[36]葛锐:《英语红学研究纵览》,《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期。
[37]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是目前国内唯一提供国外高质量学位论文全文的数据库,主要收录来自欧美国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目前中国境内可以共享的论文已经达到304781篇,涉及文、理、工、农、医等多个领域。
[38]Laurence Wong,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ng Me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uid Hawkes's English Version,Graduate Department of East Studies,University of Toronto,1992,pp.212-305.
[39]姚琴:《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意义显化考察——以霍译本林黛玉人物特征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刘泽权、朱虹:《〈红楼梦〉中、英文本中刘姥姥形象的对比——以刘姥姥话语的人际功能分析为例》,《翻译季刊》2007年第44期。
[40]刘泽权、田璐:《红楼梦叙事标记语及其英译——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外语学刊》2009年第1期。
[41]刘泽权、闫继苗:《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3期。
[42]刘泽权、朱虹:《〈红楼梦〉中、英文本中刘姥姥形象的对比——以刘姥姥话语的人际功能分析为例》,《翻译季刊》2007年第44期;刘泽权、赵烨:《〈红楼梦〉人物“哭态”探析》,《河北学刊》2009年第29期。
[43]欧阳健:《眼别真赝 心识古今——和蔡义江先生讨论〈红楼梦〉版本》,《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期。
[44]郑向前:《〈红楼梦〉早期抄本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
[45]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6]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7]陈宏薇将《红楼梦》英译事业分成三个阶段,但只阐释了9种英译本,而江帆在其博士论文中阐释了11种英译。参见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48]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49]另见王金波、王燕《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期。
[50]E.C.Wener,“Correspondenc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The China Journal,Vol.VI,No.4,April,1927,pp.175-177.
[51]吴世昌:《书目甲·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及论著》,载吴世昌《吴世昌全集第七卷·红楼梦探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5页。详见第385页“我未见威氏译文,未列入本书目”。
[52]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3]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4]David Hawkes(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Vol.3,1980,the cover.
[55]David Hawkes(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Vol.1,1973,the cover.
[56]Howard Goldblatt,“(Untitled Review)Cao Xueqin.The Story of the Stone.1:The Golden Days.2:The Crab-Flower Club.David Hawkes(tr.),Bloomington,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China,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54,No.2,Spring,1980,p.333.
[57]林煌天:《中国翻译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4页。
[58]许国璋:《借鉴与拿来》,《外国语》1979年第3期。
[59]Gladys Yang,“(Untitled Review)David Hawkes(tr.):The Story of the Stone.A Novel in Five Volumes by Cao Xueqin.Vol.I:The Golden Days.Vol.II:The Crab-flower Club.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Reuiew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43,No.3,1980,pp.621-622.
[60]M.Baker,“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Target,Vol.7,No.2,1995,p.234.
[61]David Hawkes(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Ⅰ-Ⅲ),London:The Penguin Books Ltd.,1973,p.18.
[62]David Hawkes(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Ⅰ-Ⅲ),London:The Penguin Books Ltd.,45-46.
[63]王宏印:《试论霍译〈红楼梦〉体制之更易与独创》,载刘士聪、崔永禄等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64]此处指上面引文b。
[65]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66]姜其煌:《〈红楼梦〉霍克斯英文全译本》,《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
[67]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68]洪涛:《〈红楼梦〉翻译研究与套用“目的论”、“多元系统论”的隐患——以〈红译艺坛〉为论析中心》,《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2期。
[69]David Hawkes,“The Translator,the Mirror and the Dream—Some Observations on a New Theory”,in John Minford & Siu-kit Wong(ed.),Classical,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p.159.
[70]转引自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71]Connie Chan,“Appendix: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A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Conducted at 6 Addison Crescent,Oxford,December,1998,p.327.
[72]转引自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7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共四册),启功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74]本次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英文部分以霍克斯先生翻译的企鹅出版社《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Penguin Books)1973年版第一卷、1977年版第二卷、1980年版第三卷为底本,参照霍克斯先生《红楼梦英译笔记》(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及相关日记、书信,对现有译文做了全面系统的校订。中文部分则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竖排版(启功校注)为底本,主要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甲戌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有正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梦稿本),这些都是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参考过的本子。
[75]Cao Xueqin&Gao E.,A Dream of Red Mansions,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p.ix.
[76]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载刘士聪、崔永禄等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77]Cao Xueqin & Gao E.,A Dream of Red Mansions,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
[78]“脂京本”即庚辰本,是吴世昌先生“为了批评胡适而提出来的”,后来遭到红学家冯其庸的质疑,详见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51页)“关于所谓‘脂京本’的名称问题”一节。
[79]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7—488页。
[80]王丽娜:《〈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翻译与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1992年第1期。
[81]洪涛:《评“汉英经典文库本”〈红楼梦〉英译的疏失错误》,《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期。
[82]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83]如水:《记杨宪益先生》,载《银翘集》,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6页。
[84]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85]Kennedy,G.D.,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London/New York:Longman,1998,p.60.
[86]程乙本电子版来源:http://bbsopenow.net/showthread.php?s=c12211171cb4d6a5299c a6a32fdf6756&t=43473。
[87]杨、霍译本电子版均系冯庆华教授携同众位弟子合力扫描并校对后得出,在此一并致谢。
[88]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L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43.
[89]A.Mauranen& P.Kujamaki(eds.),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p.1.
[90]A.Chesterman,“Beyond the Particular”,in A.Mauranen and P.Kujama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A.Chesterman,“Hypothesis about Translation Universals”,in G.Hansen,K.Malmkjar and D.Gile(ed.),Claims,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Selected Contributions for the EST Congress,Copenhagen,2001,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91]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92]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L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43.
[93]R.Vanderauwera,Dutch Nou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The Transformation of A“Minority”Literature,Amsterdam:Rodopi,1985; S.Blum-Kulka,“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in J.House & S.Blum-Kulka(ed.),Inter-lingual and L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86; M.Shlesinger,“Interpreter Latitude VS Due Process: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Lnterpretation in Multilingual Trials”,in S.Tirkkonen-Condit(ed.),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Lntercultural Studies,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91.
[94]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L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p.243-245.
[95]M.Baker,“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in H.Somers(ed.),Terminology,LSP and Translation,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6,pp.176-177,180-185.
[96]参见 G.Hansen,K.Malmkjer & D.Gile(eds.),Claims,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A.Mauranen & P.Kujamaki(eds.),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97]Elisa Perego,“Evidence of Explicitation in Subtitling:Toward a Categoriz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4,No.1,2003,p.68.
[98]Jean-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Comparatiu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an C.Sager & M.J.Hamel,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58/1995,p.342.
[99]E.A.Nida,& C.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p.164-165.
[100]Blum-Kulka,S.,“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in J.House &S.Blum-Kulka(ed.),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86,p.19.
[101]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43.
[102]M.Baker,“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in H.Somers(ed.),Terminology,LSP and Translation,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6.
[103]Candace Séguinot,“Pragmatics and 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TTR Traduction,Terminologie,Redaction,Vol.1,No.2,1988,pp.106-113.
[104]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05]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106]Anthony Pym,“Explaining Explicitation”,http://www.fut.es/-apym/welcome.
[107]K.Klaudy & Krisztina Károly,“Im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6,No.1,2005,pp.13-28.
[108]Elisa Perego,“Evidence of Explicitation in Subtitling:toward a Categoriz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4,No.1,2003,p.69.
[109]Elisa Perego,“Evidence of Explicitation in Subtitling:toward a Categoriz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4,No.1,2003,p.70.
[110]黄立波、王克非:《翻译普遍性研究反思》,《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
[111]S.Laviosa,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y,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Amsterdam:Rodopi,2002.
[112]M.Olohan,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
[113]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p.233-250.
[114]Jean-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Comparatiu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an C.Sager & M.J.Hamel,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58/1995.
[115]E.A.Nida & C.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p.164-165; E.A.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64/2004.
[116]R.Vanderauwera,Dutch Nou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The Transformation of a“Minority”Literature,Amsterdam:Rodopi,1985.
[117]S.Blum-Kulka,“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in J.House & S.BlumKulka(ed.),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86,p.19.
[118]K.Klaudy,“Explicitation”,in M.Baker(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8.
[119]See S.Laviosa,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y,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Amsterdam:Rodopi,2002,p.1.
[120]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p.233-250.
[121]Baker,Mona(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4.
[122]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43.
[123]M.Olohan & M.Baker,“Reporting That in Translated English:Evidence for Subconscious Process of Explicit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1,2000,pp.141-172.
[124]M.Olohan,“Spelling out the Optionals in Translation:A Corpus Study”,UCREL Technical Papers,Vol.13,2001,pp.423-432; M.Olohan,“Leave It Out! Using a Comparable Corpus to Investigate Aspects of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Cadernos de Traducao,Vol.IX,2002,pp.153-169; M.Olohan,“Comparable Corpora in Translation Research:Overview of Recent Analyses Using the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http://www.iff.unizh.ch/cl/yuste/postworkshop/repository/molohan.
[125]M.Olohan,“How Frequent are The Contractions? A Study of Contracted Forms in The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Target,Vol.15,No.1,2003,pp.59-89.
[126]T.Puurtinen,“Syntax,Readability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Meta,Vol.43,No.4,1998,pp.524-533; T.Puurtinen,“Genre-specific 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ed and Non-translated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Vol.18,No.4,2003,pp.389-406; T.Puurtinen,“Nonfinite Constructions in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 Contradicting Translation Universals”,in S.Granger,J.Lerot & S.Petch-Tyson(ed.),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u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Rodopi,2003.
[127]胡显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小说词语特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王克非、胡显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128]“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王克非主持建设。该语料库库容量达3000万字词,由翻译、百科、专科和对译语句四个子库构成。其中,翻译文本库容量为2000万字词,英译汉占60%,汉译英占40%,分别含文学和非文学语料。全部语料进行了句对齐和词性标注,可分类检索和考察词频、搭配等。文学语料中以小说为主。
[129]J.Schmied& H.Schffler,“Explicitness as a Universal Feature of Translation”,in M.Ljung (ed.),Corpus-based Studies in English.Papers from the 17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on Computerized Corpora(ICAME 17)Stockolm,May 15-19,199,Amsterdam:Rodopi,1997,p.21.
[130]L.Øver·a s,“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eta,Vol.43,No.2,1998,pp.568-588.
[131]Elisa Perego,“Evidence of Explicitation in Subtitling:Toward a Categoriz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4,No.1,2003,pp.63-88.
[132]柯飞:《汉语“把”字句特点、分布及英译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2期。
[133]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4]王克非:《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库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
[135]A.Frankenberg-Gacia,“Are Translations Longer Than Source text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Explicitation”,2004,http://www.academia.edu/3260827.
[136]K.Klaudy & Krisztina Károly,“Im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6,No.1,2005,pp.13-28.
[137]K.Klaudy & Krisztina Károly,“Im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6,No.1,2005,p.14.
[138]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139]Ewa Gumul,“Explicit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Strategy or a By-product of Language Mediation”,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es,Vol.7,No.2,2006,pp.171-190.
[140]Birgitta Englund-Dimitrova,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
[141]Vilma Papai,“Explicitation:A Universal of Translated Text”,in A.Mauranen &P.Kujamu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142]M.Baker,“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Target,Vol.7,No.2,1995,p.234.
[143]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p.240-241.
[144]Saldanha Gabriela,“Translator Style: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Translator,Vol.17,2011,p.27.
[145]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146]胡开宝:《语料库翻译学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147]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43.
[148]S.Bernardini & F.Zanettin,“When is a Universal not a Universal? Some Limits of Current Corpus-based Methodologi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in A.Mauranen and P.Kujama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149]D.Kenny,Lexis and Creatiuity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Manchester:St.Jerome,2001; D.Kenny,“Parallel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Studies:Old Questions,New Perspectives? Reporting That in Gepcolt:A Case Study”,in G.Barnbrook,P.Danielsson &M.Mahlberg(ed.),Meaningful Texts:The Extraction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Mono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rpora,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2005.
[150]黄立波、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151]黄立波、王克非:《翻译普遍性研究反思》,《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
[152]黄立波、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153]黄立波、王克非:《翻译普遍性研究反思》,《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
[154]M.Baker(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4.
[155]吴昂、黄立波:《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156]Gideon Toury,“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Welcome as They Are,Would they Qualify as Universals”,in A.Mauranen & P.Kujama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157]李希凡、李萌:《“可叹停机德”——薛宝钗论》,《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2期。
[158]Laurence Wong,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ng Me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uid Hawkes's English Version,Graduate Department of East Studies,University of Toronto,1992,p.10.
[159]Laurence Wong,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ng Me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uid Hawkes's English Version,Graduate Department of East Studies,University of Toronto,1992,p.517.
[160]黄立波、王克非:《翻译普遍性研究反思》,《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
[161]L.Øver·as,“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An Investigation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eta,Vol.43,No.2,1998,pp.571- 588; M.Olohan & M.Baker,“Reporting That in Translated English:Evidence for Subconscious Process of Explicit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Vol.1,2000,pp.141-172.
[162]刘泽权、侯羽:《国内外显化研究概述》,《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
[163]D.Noel,“Translation as Evidence for Semantics:An Illustration”,Linguistics,Vol.4,2003,pp.757-785.
[164]卫乃兴:《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短语学研究》,《外国语》2011年第4期。
[165]W.Teubert,“Directions in Corpus Linguistics”,in Halliday,M.A.K.,Wolfgang Teubert,Co-lin Yalop & Anna Germakova(ed.),Lexicology & Cor-pus Linguistics,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2004.
[166]M.Tymoczko,,“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eta,Vol.XLIII,No.4,1998,pp.1-8.
[167]王克非、黄立波:《语料库翻译学的几个术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68]M.Baker,“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 M.Baker,G.Francis and E.Tognini-Bonelli(ed.),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Philadelphia &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p.235.
[169]S.Laviosa,“The Corpus-based Approach: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Meta,Vol.43,No.4,1998,p.474.
[170]Geoffrey Leech,“Teaching in Language Corpora:A Convergence”,in Gerry Knowles,Tony McEnery,Stephen Fligelstone&Arme Wichman(ed.),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London:Longman,1997,p.22.
[171]Susan Hunston,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28.
[172]Noelle Serpellet,“Mand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 Their Equivalents in French:Applying a Bilingu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in Bemhard Kettemann and Georg Marko(ed.),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Doing Corpus Analysis,Procee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Amsterdam & New York,2002,pp.359-360.
[173]A.Chesterman,“Beyond the Particular”,in A.Mauranen and P.Kujama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p.33.
[174]S.Laviosa,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y,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Amsterdam:Rodopi,2002,p.2.
[175]S.Bernardini& F.Zanettin,“When is a Universal not a Universal? Some Limits of Current Corpus-based Methodologi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in A.Mauranen and P.Kujamaki(ed.),Translation Uniuersals:Do They Exist?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176]L.Øver·as,“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eta,Vol.43,No.2,1998,pp.571-588; D.Kenny,Lexis and Creatiuity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Manchester:St.Jerome,2001; D.Kenny,“Parallel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Studies:Old Questions,New Perspectives? Reporting that in Gepcolt:A Case Study”,in G.Barnbrook,P.Danielsson & M.Mahlberg(ed.),Meaningful Texts:The Extraction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Mono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rpora,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2005.
[177]H.Hasselgard,“Using Parallel Corpora in Contrastive Studies:Cross-linguistic Contrast of Future Referring Expressions in English and Norwegian”,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Vol.1,2012,pp.3-19; S.Johansson,Seeing Through Multilingual Corpora:On the Use of Corpora in Contrastiue Studi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7.
[178]Michael Stubbs,“British Tradition in Text Analysis from Firth to Sinclair”,in M.Baker,G.Francis & E.Tognini-Bonelli(ed.),Text amd Technology: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3,p.24.
[179]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180]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中国外语》2012年第1期。
[181]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中国外语》2012年第1期。
[182]刘泽权、田璐:《红楼梦叙事标记语及其英译——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外语学刊》2009年第1期。
[183]王宏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建立“〈红楼〉译评”的宏伟目标而努力》,载刘士聪、崔永禄等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487页。
[184]张美芳:《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贝克研究新法评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