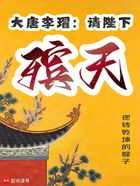
第1章 江山棋局谋权柄
大唐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阴。(公元740年11月4日)。
长安永福坊寿王宅。
此刻中门大开,香案俱备。
边令诚手持拂尘,站在香案旁边,手中拿一份黄麻纸写就的敕令,朗声道:“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底下久久不闻有声,边令诚看向依旧跪着的寿王,目光冷漠,知道他心中不好受,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圣人眼皮底下独占美人,终究是会招祸的。
“寿王接诏吧。”边令诚高声提醒。
寿王李瑁安静地听完这道著名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之后,这才缓缓抬头,脸上神情纯良无辜:“臣实在不知如何接这道诏令。”(注1)
边令诚目光中闪过一道阴狠的光:“寿王莫非想违诏?”
出发之前,他就已做好了万全准备,为防李瑁暴起,特地找了高力士,得了他的准,点了左羽林军三百人随行,此刻已将整片永福坊十六王宅团团围住,前前后后水泄不通。
一旦李瑁有任何不敬之举,当场就可拿下问罪。
最好是问罪,这样李瑁就再无登上储君之位的可能,而杨玉环的名分问题也可顺理成章地解决掉了,在圣人那里可是大功一件。(注2)
一名内侍居然敢带兵威胁皇子,放在别的朝代都是咄咄怪事,不过如果那人是高力士的干儿子,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儿子再亲,不如身边的宦侍亲。
李瑁神色平静:“臣不敢违诏,但不知怎么接诏。”
边令诚打量着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这有什么不知的?让你的王妃赶快准备一下,准备去骊山宮迎驾就是了。”
自此后,其璧归属,就当易主了。
李瑁言辞恳切道:“还请边中官禀明陛下,再给臣几日时间,臣一定想办法把杨氏找出来。”
边令诚一愣,任是他神机妙算,也没算到是这种回答,忙问道:“寿王妃呢?”
李瑁道:“跑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葩事,边令诚呆若木鸡,站在原地,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
。
。
时间回到十天前。
刚刚穿越的李瑁懵逼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原主寿王的记忆如潮水汹涌,奔袭而来。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记忆全部理清。
他的母亲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在世时三千宠爱在一身,位同皇后。
武惠妃一直心心念念要将儿子推上太子之位,三年前趁张九龄被贬之机,联合李林甫,指使女婿、驸马都尉杨洄诬告皇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三人结党谋反。
而李隆基原本就想打击日渐做大的太子党,便顺势将三人废为庶人。
甚至旋即又在李林甫的拱火之下,将三人一一赐死,造成了所谓的“三庶人”冤案。
但纵然武惠妃和李林甫费尽心机,寿王立储的事,李隆基最终也没点头应允。
武惠妃因此郁郁寡欢,屡被“三庶人”的鬼魂所扰,居然在同一年也撒手人寰,带走了李隆基全部的宠爱,将寿王留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武惠妃逝去才几个月后,李隆基就听取高力士的建议“推长而立”,反手立了三皇子忠王李亨为太子,这让曾经试图夺嫡的寿王李瑁更加难以自处。(注3)
想到这里,李瑁打了个寒战。
武惠妃死后,李隆基无精打采,高力士为解君忧,决定下手抢儿媳妇。
而他李瑁,正是那个倒霉儿子,将要被抢的儿媳妇也就是寿王妃杨玉环。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初,熟悉这段历史的他,知道这正是李隆基召杨玉环入宫,以女道士杨太真的身份伺候他的前夕。
杨玉环这会儿还没入宫,只是入宫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这就是原主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被老爸戴了绿帽。
现在的李瑁对此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杨玉环,他只在乎江山。
既然如此,杨玉环就得除掉!
并不是李瑁在乎头上那青青草原,而是他知道,入宫后的寿王妃杨玉环,和她公爹为了名正言顺地双宿双栖,会不断的打压他这个寿王,绝不会让他有出头之日。
懦弱的原主束手无策,只能忍气吞声,窝窝囊囊地过完了一辈子。
同时,也见证了盛唐转衰的全过程,亲眼看着原本如日中天、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快速沦落为藩镇割据、战乱连天的破碎王朝。
然而,作为一个时刻准备着接班的现代人,李瑁的性格中就没有“怂”这个字。
他早年初入职场,受尽霸凌,随后觉醒,努力修炼各种揣摩人心的技术,投身于勾心斗角的阴谋算计之中。
他先后将霸凌于他的上级一个个掀翻在地,最后更是攀上贵人,摇身一变成为单位说一不二的一哥。
当年为了修炼谋略,他常常翻看史书。
每每看到盛唐转衰,强大帝国昙花一现,转眼间风雨飘摇,就忍不住扼腕叹息。
每每想到外族劫掠,民不聊生,内战连连,饿殍遍野,与贞观时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形成鲜明对比,他总是忍不住痛骂李隆基的短视无能。
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若自己能统御大唐,岂能让这盛世草草完结?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听到了这番心声,居然真的让自己穿越了,这是上天也看不过眼,悲悯盛唐陨落,民不聊生,所以让自己过来力挽狂澜的吗?
李瑁心念电转,一算时间,开元盛世已到末期,但距离安史之乱则还有整整十六年。
那场动乱,大唐风雨飘摇,由盛转衰,从此辉煌不再。
不仅给大唐造成了无法自愈的伤口,也从此埋下了无法解决的诸多祸患。
史学家认为,如果安史之乱不爆发,那么大唐或许不至于衰落得那么快,因此安禄山是终结盛唐的罪魁祸首。
但李瑁认为,安史之乱不发生,李隆基就会继续盘踞在九五之尊的位置上,宠幸奸佞,一味倒行逆施。
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安福山,而百姓苦不堪言,迟早也会发生民变,所以李隆基才是这一切的元凶巨恶。
大唐终究还是要颠覆,山河还是要陷于战火之中。
要想解救盛唐,庇护众生,治本之策就是得先把李隆基给干掉,而且最好以一个成本可控、不损元气的方式干掉。
他李瑁既不愿看到泱泱华夏陷入数百年的混乱不堪,生灵涂炭,更不想自己只能做个闲散亲王,畏畏缩缩的袖手旁观,白白蹉跎一生。
何况对于平庸之人,那是一场浩劫,可对于韬略雄主,却是问鼎至尊的最好时机。
武惠妃没能争来的储君之位,靠自己直接一步到位不是更潇洒快意?
如今唯一的问题在于,十六年真是太TM长了!
得加快!
李瑁眉头一皱,决定先解决杨玉环再说。
开元末年,李隆基登基日久,皇权稳固,虽然他后期渐渐昏聩,将大好局面白白葬送,但不见得他就是个平庸的帝王。
相反,他二十五岁便能诛杀韦后集团,屠灭太平公主,逼迫父亲李旦让位,创立开元盛世,恰恰证明他天资禀赋,工于心计手段。
与这样一只猛虎周旋,只可智取,不能力拼,否则无异于以卵击石。
若想解决杨玉环,事后又能不违诏,需要找一个好借口。
一个不管离不离谱,但能真实发生,且不会归罪自己的借口。
于是有了边令诚宣诏后的那一幕。
边令诚完全不相信李瑁所言,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内宦,没有明诏,还能带着羽林军直接搜十六王宅不成?
他只当李瑁不愿交出杨玉环,诡词狡辩,于是把脸一沉,对跟在身后的羽林军校尉道:“你们且候在这里,待我回宫请诏再说。”
那校尉本就归附高力士,自然对他的干儿子边令诚也当成祖宗供奉,所谓“候在这里”,其实就是继续包围寿王宅,让李瑁插翅难飞。
校尉忙拱手道:“中官放心,末将绝对不敢擅离职守。”
。
。
。
东内大明宫紫宸殿。
李隆基刚刚和群臣议完事,有些疲乏,正叫人拿了一个九龙锦黄垫子靠着,让小内侍捶腿。
边令诚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不敢惊扰圣人,只在旁边候着。
等着高力士服侍圣人喝完茶,退下来洗手的时候,他才敢走过来,轻声道:“干爹,儿子有要紧事禀告。”
高力士知道他去寿王宅宣诏的事,此刻见他神情委顿,知道出了岔子,招招手,两个人悄无声息地出了紫宸殿,来到外面的游廊上。
边令诚殷勤地掏出帕子在游廊宽大的扶手上擦拭了好几下,扶着高力士坐下,作出一副哭丧脸道:“干爹,美人怕是要不过来了。”
高力士没理他那副故作姿态的表演,道:“有事说事。”
“是。”边令诚不敢再放肆,一五一十地将李瑁的回答说给了高力士听。
高力士也觉得匪夷所思:“王妃跑了?没听寿王宅使跟我报过这事啊。”说着,他低头想了一想,蓦然道:“想起来了,说是前几日王妃回娘家探亲,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敢情是那时候跑的?”
见高力士若有所思,边令诚急了:“干爹,那杨氏小门小户的,娘家又无权势,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敢如此离经叛道?分明是寿王不肯交出美人,故意拿这些离谱的理由来搪塞。这可是违诏的大罪,给圣人甩脸子。依儿子的意思,让羽林军先把他拿了,等圣人亲自问他,看他交不交?”
高力士沉下脸来斥道:“胡闹!那毕竟是亲王,你当是不入流的小官吗?”
边令诚嘟囔道:“他也就是个不受宠的亲王,要不怎么当不上太子?”
高力士脸都黑了,声音也加重了几分:“我素日怎么教你的?储君之事,也是你一个小内侍能议论的?你要是嫌命长,我明儿就让人把你办了,省得将来惹大祸。”
见高力士生气了,边令诚不敢再说,讨饶道:“干爹,儿子只在您面前说这些,外面是决计不敢议论一句的。只是现在寿王推托不接诏,儿子在圣人面前交不了差,怕是要领一顿板子了。”
高力士沉思片刻,道:“你且在廊下候着,我进去与圣人说去。”
高力士去而复返,直接在御案前跪下道:“老奴无能,请大家降罪。”(注4)
李隆基愣了一下:“怎么?出什么事了?”
高力士回禀道:“边令诚原样宣了大家的诏敕,但寿王有苦衷,说寿王妃离宅多日,不知踪影,他也还在找人,所以接不了诏。还请大家宽限几日,老奴派人去四处查探,务必找到寿王妃所在。”
李隆基听得一怔,这理由未免过于离谱,且时机又过于巧合。
他不由得怀疑起李瑁是否因立储未成一事早已心怀不满,借机反抗,藐视皇权,却丝毫没虑及自己强抢儿媳妇之举有多么离大谱。
想及此处,李隆基胸口顿起冒起了一阵无明火,冷笑一声,对高力士道:“即刻宣李瑁进宫见朕。”
——————————————
以下考据可跳过,谨供书友参考
——————————————
『注1:关于寿王的名字李瑁』
据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考据了开元二十五年的《唐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所附诸王列名,以及武惠妃碑文中寿王的名字,均为“琩”。然本书主要参考史料为:新、旧唐书、通鉴,以及会要和六典,其中均明确玄宗为各皇子多次改名之后,十八子寿王最终用的是李瑁这个名字。再考虑当今大量影视剧作中也是采用李瑁这个名字,故为方便阅读,本书统一为李瑁。
另,欧阳修个人虽考据出了“琩”字,但他主持编写新唐书时却仍然用的是“瑁”字,应是类似考虑。
『注2:关于杨贵妃的名字杨玉环』
杨贵妃作为中国古代四美之“羞花”,祖籍关中望族弘农杨氏,后迁往蒲州永乐,幼年随其父杨玄琰在蜀地生活,后父母双亡,由三叔杨玄璬在洛阳养大,于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被玄宗册立为寿王妃,又于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以为太后追福之名入宫为女道士,号“太真”,宫中尊称“娘子”,待五年后风声过去,玄宗才正式册封她为贵妃。以上在《新唐书》及《通鉴》中吻合无疑。但她的真名则说法较多,如《全唐文》中“杨妃小名玉娘”,《明皇杂录》中“杨贵妃小字玉环”,《容斋续笔》中“杨贵妃小名玉奴”等等。
不过杨贵妃最广为公众所知的名字仍是杨玉环,故为方便阅读,本书统一为杨玉环。
『注3:关于太子的名字李亨』
李亨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仁孝好学,过目不忘,但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其在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废太子李瑛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六年被立为太子,当时叫李玙。开元二十八年改名李绍,天宝三载最终改名李亨——《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新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因其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李亨,故为方便阅读和情节开展,本书统一为李亨,去掉其反复改名的史实。
『注4:关于唐代君臣的称呼』
据新、旧唐书及通鉴,有唐一代,人们言谈间提及皇帝时都是“圣人”或“陛下”,外臣或正式场合觐见皇帝时一般称呼“陛下”,内侍或私下面对皇帝则可称“大家”;反过来,皇帝一般在正式场合自称“朕”,但在私下则自称“吾”或“我”。另,皇帝称呼别人一般是“汝”或“你”甚至“卿”,称皇子则为“吾儿”或“我儿”;而皇子对皇帝则自称“儿”或“臣”;他朝流行的“儿臣”、“父皇”、“皇上”等都是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