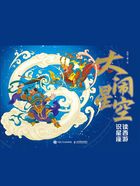
西方星座东传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自古有之,玄奘取经就是中外交流的佳话。秦汉以降,中外天文交流逐渐增加,巴比伦、希腊、印度的天文学知识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西方星座知识最早在隋唐时期与佛经一起传入中国,隋代《大乘大方等日藏经》首次出现了意译的黄道十二宫名称。佛经中的黄道十二宫都是预测个人命运吉凶的星占内容,正好填补了中国没有此类星占的空白,从隋唐到宋元风行中土数百年,至今我们仍能在敦煌壁画、河北宣化辽墓星图等一些文物中看到本土化的黄道十二宫形象。
十三世纪,蒙古铁蹄横扫亚欧大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日渐频繁,伊斯兰的天球仪和星占书籍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明初的天文书籍曾出现过20多个西方星座名称。从元初至明末近400年的时间里,伊斯兰天文学作为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补充和参考,在仪器制造、历法编制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天文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托勒密48星座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三垣二十八宿,仅仅是不同的恒星命名体系,并无本质差异,且与中国传统天文体系格格不入,因此并没有被国人所接受。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至沓来,西方星座第三次被带到中国。徐光启领导编制《崇祯历书》时,中国学者已经知道西方有62个星座,即托勒密48星座、航海12星座外加南十字与天鸽两座。此时中国星座还不包括南天极附近的区域,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岂能放任这片区域一直是空白呢?于是汤若望、罗雅谷等西方传教士将航海十二星座等以中国人更熟悉的方式重新划分为23个星座,改弦更张纳入中国星座体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结束闭关锁国的历史,完整的西方星座知识与最新天文研究成果一起被介绍给普通的中国读者。1911年,辛亥革命后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中国传统星座遭到冷落,天文研究领域逐步使用西方星座。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同年国际天文联会正式确定国际通用的88个星座,随后又划定星座界限,新的国际通用星座为现代天文研究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天区划分方案,而中国传统星座仍然停留在恒星组合阶段,早已无法胜任望远镜发明之后暴增的恒星和各类天体命名任务。加上国际天文交流需要统一的语言,国际通用星座因此被刚刚成立的中国天文学会接受,标准的星座译名随之确立。中国传统星座被摒弃,只有大角、心宿二、轩辕十四等亮星的星名还在沿用。

★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两侧炽盛光佛壁画中的黄道十二宫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