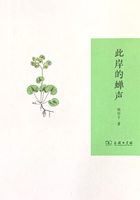
重读与精读
一、重读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比阅读更好的事,是重读。他说:“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我要劝大家少读新书而更多地重读。”博尔赫斯喜欢反复读一些早年读过的书,温故知新,自得其乐。他回忆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读了第一遍,以后就反复读下去。当然,他提醒读者,《堂吉诃德》的精彩在第二部,第一部除了第一章,其他都可以略去。这样终生爱不释手的书,还有斯蒂文森的作品,还有《神曲》《一千零一夜》,吉卜林和切斯特顿的小说,以及瑞典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和叔本华、贝克莱、休谟等哲学家的著作。
孔子说温故知新,后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但最重要的一点,毫无疑问的,是温习旧学,有新的领悟。朱熹解释说:“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无穷。”读书一在精,一在博。精博的境界,在于贯通。重读,除了个人喜爱的原因,如博尔赫斯之于斯蒂文森,苏东坡之于《汉书》,是读透和悟彻一本书的必由之路。温故而知新,就是精。
朱子论读书,言语多,又切当。他反复强调的几个方面中,就有“熟读”和“透彻”: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
三条说的是一个意思:熟读精思,对于书中所言,穷追猛打,一竿子捅到底:“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朱子说,读书,先要杀进去,而后,还要杀出来。读通了,想透了,自然远近随心,进出如意:“看文字,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
读书,大多数时候是浮在表面的,好像游泳,在水面上扑打蹬踢。读懂了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段话,尽管已经是很认真地阅读,就像游泳沾湿了身体的每一部分一样,但若止于此,就还是浮着的。进去,是有所领悟了,有所得了。而脱离,才是第三重境界:由他人而返归自我,博观约取,消化吸收,如此才能“其应无穷”。
东坡读书,有“八面受敌”之法:
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读,但得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也就是说,一部书其中涉及很多方面的学问,一次读,集中精力于其中一个方面,把这一方面彻底弄懂。郭沫若说他读先秦诸子,读一遍,看他如何说政治;再读,看他如何说社会伦理;接下去,看他如何说历史观、人性论,等等。大意如此。这也就是东坡的“八面受敌”法。朱熹很欣赏东坡这段话,教导学生以此为楷模。
博尔赫斯大概没读到过东坡的话,也没读到朱子的话,如果读到了,是必要引为知音的。我读到博尔赫斯的话,想起孔子、东坡、朱子,自然莫逆于心。几十年的阅读经验,证明了这些话说得多么好。
中国和西方的典籍,很多都是可以终生阅读、受用无穷的。一个人脑子里如果没有几十部读懂读通了的书,不离不弃,一辈子重温不已,仿佛家乡或根据地,又仿佛一个宝库,取用不尽,作为安身立命的场所,那么,涉猎再多,只如满天花雨,往好了说,不过图个好看罢了。
《庄子》读了一辈子,《西游记》我读了至少十几遍,仍然爱不释手。唐诗宋诗像茶或咖啡,几乎一日不能搁下。全部的唐人小说,恨不得永远读不完。《世说新语》,随时想起来,翻到任一页,读两条,往往心满意足。曾和朋友说,读一部《水浒传》,胜过读杂书一百。这话一点也没夸张。相反,说得太保守了。
二、江湖无碍人之心
宗璞《东藏记》第四章写到英伦留学回来的夫妇尤甲仁和姚秋尔,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言谈之间,钱明经有意探探尤甲仁的底,出了个小题目考他:
钱明经忽发奇想,要试他一试,见孟先生并不发言,便试探着说:“尤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外国东西是熟的了,又是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东西更熟,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明经点头道:“最后的‘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所以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有些道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明经想着,还要再问。
这个尤甲仁,有人说是影射一位大学者的,但这位大学者学问之渊博,一般人未必深知,恐怕不是轻易好嘲讽的。《诗品》并非多难的题目,别说这位大学者,读过的人都能谈出点看法。这里就小说的虚构情节而论,只当尤甲仁是尤甲仁,满脑子学问,却没有自己的见解。周作人说,这种读书人,不过一个“两脚书橱”。写出的文章,尽管旁征博引,是“獭祭”,一种水边小动物玩的把戏。
叔本华论读书的话,因早年读鲁迅而知,印象很深。鲁迅在《华盖集》的《碎话》里引述道:
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这段话出自叔本华的《论阅读和书籍》,后文说:
在阅读的时候,思维的大部分工作是别人帮我们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从专注于自己的思想转入阅读的时候,会明显感受到某种放松。但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也就成了别人思想的游戏场。当这些东西终于撤离了以后,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这样,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时候只稍作不动脑筋的消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最终会失去走路的能力一样。
叔本华并不反对读书,他强调的是读书时的思考。他的傲慢在于,他显然觉得大多数人的阅读是“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脑袋里跑马。”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一个人再不肯动脑筋,读到的哪怕是再烂的书,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是会有一点的——即使是负面的影响。再说了,通过阅读而知道更多的东西,比方“多识鸟兽虫鱼之名”,也比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叔本华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来说这些话的,他的貌似刻薄其实并不刻薄,相反,几乎是温情脉脉的:
只有经过重温和回想,我们才能吸收阅读过的东西,正如食物并非咽下之时就能为我们提供营养,而只能在消化以后。如果我们经常持续不断地阅读,之后对所读的东西又不多加琢磨,那些东西就不会在头脑中扎根,大部分我们都会遗忘。
形诸文字的思想,从无绝对的正确。因为任何思想,都是出自一个和我们一样靠“吃五谷杂粮”维系的头脑。我们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一样。我们为了达成某种目的,会改变述说的方式,突出一些内容,掩藏和美化一些内容。我们会说谎,他人亦然。思考就是透过文字看清这一切,在从他人的智慧获益的同时,又不为他人牵制。宋朝的禅师说,人牵着自己的心,好像牵着一头牛,一番奔波,安然归家,最后人牛俱忘。但要记住,你自己不能变成牛,被别人牵了鼻子走。
《景德传灯录》卷十七有湖南龙牙山居遁禅师的一段对话。有僧人问居遁:祖佛有没有骗人之心?他说:我先问你,江湖有没有阻碍人之心?僧人大概回答说没有吧。居遁禅师就给他讲:江湖虽然没有阻碍人之心,但江湖横在那里,人过不去,它确实阻碍人了,不能说江湖不阻碍人。祖佛虽然没有骗人之心,可是,人如果读不懂、读不透,祖佛等于把人骗了,不能说祖佛没有蒙骗人。“若透得祖佛过,此人过却祖佛也,始是体得祖佛意,方与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学佛学祖,则万劫无有得期。”
这段话说读书的道理,极为通透。著书者本存善意,读者若一味痴信,不独立思考,自家迷途,就怨不得别人了。读书,单单一个多字,那是远远不够的。
附记:《诗品·清奇》一节的全文是:“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屟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此处描写的是一种清幽的意境,也可以说有点空寂,但清幽空寂中透着从容和闲逸,与所谓“凄凉”真是八竿子打不着。不知这钱明经是如何读书的。
三、两种书
人和书一样,有很多类别,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你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喜欢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喜欢就是更高的好。但事物之间,分离聚合,有因缘在。时候到来,机会合适,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恰如其分,自然建立起某种关系,达到所谓契合。人活到后来,学会的无非是懂得:得到可以有很多种层次、很多种方式,而且不一定是得到。得不到也是一种得到。一件事,你悬想十年,无数焦虑和喜悦在里头。那些日子,你觉得充实,不会无聊。十年下来,一切可能被你想尽,所有细节被你反复揣摩,它影响你、改变你。因为这件事,你的生活被暗中替换了,你不再是原先的自己。这个时候,实际的得与不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世上有一类书,它的好处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展示出来的。就像我们曾经喜欢过无数首歌,可是等我们老了,常在心头哼唱的,只剩寥寥几首,那才是真正使我们没世不忘的歌,是萦系了我们最珍贵的情感的歌。一件事,在当初,附加了太多和情势、和处境、和一时的得失相关的东西。我们衡量它,是和这些附加物一起衡量的。我们自己如此,别人又当如何。
书有两种,好的和不好的。好书的命运也有两种,终于被认知和彻底毁弃了的。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收藏了大量手稿,它们可能要在那里等上几百年上千年,才会遇到一个喜欢它的人,雕版印刷,著文推荐。也许需要更长时间。但只要图书馆还在,机遇总是存在的。有的书运气实在不好,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有无数的孤本书失传。命定的百年后将会欣赏它的人,与它再也没有一次神奇的邂逅了。比如在中国,那些失传的书完全可以写成另外一本文学史,而绝不比现在的文学史逊色。有一些人,我们知道名字,但已无法有任何表示。还有一些,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可能在偏僻的乡间,或者虽然身在都市,却是在无人知晓的陋巷,终生的心血不过是一堆乱纸,被老鼠咬碎做了软暖的小窝,被小铺子的人拿去包肉饼、包猪下水,被填塞进灶膛,化作几分钟的火焰。如果世上的所有写作都出自天命,都是神灵们的意志,毁灭又是为了什么?
四、记忆的秘诀是喜爱
头脑是个人最可信赖的图书馆。我买书不多,没有书房,有朝一日再次远迁,现有的微不足道的藏书,还将散失殆尽。假若如此,我不会觉得太惋惜,原因有二:一、基本的书可以再买;二、我信任自己的记忆。
网络尚未普及的时代,初来纽约,手头中文书不过三几本,写文章时需要引用,全凭记忆,就那样,也不显寒酸。有朋友问,你怎么着也能背下两百首唐诗吧。我说,那可不止,当盛年之时,差不多可以背两千首古诗词呢,现在虽然忘了很多,一千首还是有的。
这不是瞎吹,因为事情很简单:记忆的秘诀是喜爱。真心喜爱的东西,过目难忘。我从小学到高中,四处搜罗古诗,得到一首,如得一枚珍稀的邮票或古钱。抄写背诵,藏之于心。直到大学的前两年,还是如此。我忘不了那时如何从各种选本和杂书中找王维的诗,最终所得,不过四十多首而已。放在今天,随便取一本诗选就行了,就是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网上一下单,几天之内书就到手。中学时得到和借到的几本小书:《千家诗》《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全都抄录和背下来了。不抄不背怎么办呢?书还给别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谁能想到几十年之后,世界会有那样巨大的变化呢?而在当时,见一本古书,就像在大街上见到一位活生生的古人。也许这说法太夸张,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不过书少也有好处,它使人专注和热爱,记忆力超常发挥:你记住的,就是你拥有的,你过眼而没记住,等于把好东西白白丢了。
读生物系那时候,每天背一首诗,实际成绩超额。较长的诗,一天背不下来,就多背几首绝句来平衡指标。七律以内长度的诗,对照注解逐句看过,从头到尾念几遍,基本能背下来。比较难的是《诗经》,更难的是楚辞,《离骚》在读中文系时才拼命背会,但很快就记不全了。唐诗是最好背诵的,音韵显然起了作用。所以叶芝说,韵的作用是唤起回忆,是在一首诗中唤起阅读者对前面诗句的回忆。在文字书写不便的古代,口传文学只好是韵文。没有韵的话,节奏感强、音节和谐的散文,也容易记,《左传》《国策》乃至《易传》的文字,背诵都不难。
不好记的诗,还有个办法,就是抄一遍,效果真是好极了。
我时常想,假如十多岁的时候,古诗词的书唾手可得,上课要学、要考,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它们了吧。
庄子感叹生有涯而知无涯,他那时候,书相对有限,泛览一遍不难。今天的书岂止浩如烟海,我们只能取九牛之一毛。所以,对于读书,我的理想正如我对生活的要求,但求温饱罢了。算一算,这一辈子,宋朝以前的诗,唐五代五万首,唐以前一万首,不妨全部过一遍。宋诗,选读几家,加上零散的,三几万首。宋以后,随意涉猎。这样,大致能读到十万首古诗。再想多些,不是不可能,但没必要。
好诗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读过的诗,都是过眼云烟。读完一个朝代、一个流派、一群人和一个人的全部作品,也许是为了满足心中求“全”的虚荣心吧。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也是更好的原因:好奇。好奇也是不放心,想知道李白、杜甫究竟是怎么回事,名作见识过了,不那么好的作品又是怎样的?他们忧国忧民的时候如此,那么,他们天天吃饭睡觉,情形又如何?看到他们和我们有相同之处,顿时觉得踏实。他们在我们这里,才真正被接受。
诗作为诗肯定是最重要的,但诗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东西。在诗里,我们能知道唐人喜欢什么花、不喜欢什么花,宋人和他们有何不同;知道李白很白,王安石很黑,杜甫很瘦,而韩愈比较胖;知道唐代的酒价,宋人的灯节之盛;知道东坡能睡而李商隐常常失眠。这些把我们带到他们身边,带进他们的日常生活。
再好的选本也不能代替全集,再有眼光的选家也不可能和我们的心思完全一致。他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遗漏的篇目,可能恰好是我们特别需要的。
人如果只活在他自己的时代,未免单调。既然现实进入我们的经验,不过是充当了记忆的素材、铸造了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借助前人的文字而分享的生活感受和思考,同样丰富了我们的记忆和人生。这样,我们不仅生活在几千年的过去,还将生活在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字,也将成为后人的记忆,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