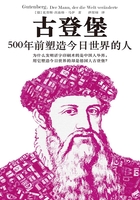
绪論 图像与原型
在古登堡出生前一个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结束旅行回到欧洲。他在外游历20年,最远曾到达中国。虽然他的游记轰动一时,但他绝非第一个探索亚洲并因此拓宽西方国家视野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人称“圣路易”)就派出了方济各会[1]修士卢布鲁克的威廉(Wilhelm von Rubruk)前往哈拉和林拜访成吉思汗之孙蒙哥(Mangu)大汗,使基督教的视线进入亚洲深处。虽然中世纪时中国、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各地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社会秩序是相同的:“个体”的概念尚未形成,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知识。一般而言,学者们不是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在教会里工作,就是服务于宗教或世俗领袖。他们身处森严的等级之中,围绕着领袖人物旋转,就像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us)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中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其他星球。
在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作者,因为每个作者都只是在阐释某个至高无上者——上帝、安拉或某个拥有真正权力的天神。此外,随处可见的还有对“哲学家”——在欧洲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则是孔子——的阐释和评论。当时也没有著作权的说法——上帝这位伟大创造者拥有世间万物的版权,有谁敢质疑这点?人们抄写书籍,靠的是勤奋和日益精进的技能。别说是拥有书籍,就连使用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从特茹河到长江,人们生活的地方丰富多样,但归根结底,人们不过是生活在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同一个世界里罢了。
这个统一的中世纪世界的瓦解自然不在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或许可以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历史来描述这个过程。但如果想用一个具体的日期和事件来标记出中世纪的转折点,那么1450年和1452年这两个年份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1450年,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1];1452年,古登堡用活字排印了《四十二行圣经》。伴随印刷复制,堪称欧洲“创始文件”的《圣经》从根本上落入了他手,这个“他”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工业”。技术革新为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深入解读文本创造了重要前提,由此也为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世俗国家和谐共存创造了基础。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理性化的基督教在欧洲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常被低估,但是自从印刷术诞生之日起,欧洲和东方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欧洲在科学技术、哲学和文明方面蓬勃发展,领先于世界的其他地区。
在欧洲,伴随着知识文本的复制及传播,知识本身也变得多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科学和文化领域之中。除了人文和艺术领域的进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数量也呈爆炸性的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缮写室和世俗的抄书坊在手抄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专业程度和效率,为书籍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直到出现机械化、分工化的复制方法,文本的获取才变得更加日常,这反过来也使得文本的生产,即文字信息的撰写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一方面,大学的数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对这些人而言,文字交流是日常行为。一切都被写了下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植物书籍到工艺教程,甚至还包括秘密。而在此之前,这一切几乎都依靠口述,很少记录在纸上。[2]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洲社会越来越多地朝着知识社会发展,文字交流成为进步的工具,而这种交流是因为古登堡才成为可能。书籍不再是奢侈品,知识不再高不可攀,伴随着著作权概念的产生,学者和作家获得了作为作者的独立性。[3]
活字印刷创造了新的交流体系,改变了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相当于今天互联网对交流和对人的地位的改变。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工具”——不论是印刷术还是互联网——“被长期运用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变化”[4]。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他的一生是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缩影,从中探寻历史转折点的痕迹正是阅读其生平的精彩所在。
然而,运用新的交流技术也意味着舍弃旧技术,与一方的胜利相伴的是另一方的失利。古登堡的发明引发了其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文化战争,因为与我们这些后人相比,他那时的人们更多地认为自己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
个体是我们现今所处社会的基础。如果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通过宗教信仰中的“我”找到了个体,那么古登堡的发明则确保了个体的存在。这个美因茨人对新世界的诞生所起到的作用远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多,也更为深远。与近东、中东和远东相比,欧洲实现了更为出色和先进的发展,欧洲因此在19世纪称霸世界。
今天,当学界说到古登堡时,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界,还是一个因古登堡而诞生的崭新星汉[5]。与此类似,互联网的出现让有些人认为“古登堡星汉”(Gutenberg-Galaxis)即将走向尽头。如果古登堡时代,即纸质书时代结束,那么由古登堡和马丁·路德开启的伟大的欧洲时代是否也将就此中止?古登堡经历了媒体和社会的巨大转变,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自己也对此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如今,我们的时代不也正面临着同样深刻的转变吗?要理解当今的转变,就必须梳理先例。因此,回溯古登堡的一生也必然是展望我们自己的未来。
探寻古登堡所处的世纪,意味着进入一个被根深蒂固的危机所笼罩的世界,意味着进入一个因变革而刹那间天摇地动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恶魔还未去神学化,是一股无比邪恶的强大力量。约翰内斯·古登堡也曾多次亲身遭遇恶魔和它的同伙。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被恶魔侵袭和附体,这样的不幸就如同遭遇冰雹或者暴风雪一般。如此一来,在恶劣天气中染上的疾病自然是恶魔的杰作,因为疾病来自恶魔和它的同伙,而痊愈和健康则被视为上帝的恩赐。
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一个被荷兰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称为“中世纪之秋”(Herbst des Mittelalters)的时代,它充满了恶劣天气、冲突、变化和戏剧性。那是一个确定之事开始变得不再确定的时代——先前那些让人们坚信基督存在的确定之事,此时不再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生活的基础摇摇欲坠。
教皇和统一帝国的皇帝是当时的两大权力中心,两者在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中相互消耗。诸侯扩张各自的领地,皇帝在帝国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落入诸侯之手;教皇则越来越像是意大利领主,而非基督代言人和基督教领袖。政治、法律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一生。
古登堡的发明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关于古登堡个人则存在较多争议。在文献资料中,他以亨内·拉登(Henne zur Laden)、亨金(Hengin)或者亨显·根斯弗莱施(Henchen Gensfleisch)的名字出现,我们面临的关于古登堡生平经历的研究困境不仅清晰地体现在不同的名字中,同样也体现在“人”(Person)这个词的本义中。
在古希腊语中,“prosopon”指的是演员的面具,观众看到的是面具,并不是演员本身的样子。古罗马人用“personare”来表示用声音穿透某物,“persona”则是面具,同时也用来表示某人在其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流传下来的约翰内斯·古登堡这个人物是历史为他戴上的面具,是在他死亡的一瞬间就已写成的传说。
他的成就如此重大,而他的生平经历中能确定的事实却如此之少,似乎也找不到任何来自他本人的文字或图像信息。难道正是这个原因,亨内的声音才微弱到不足以穿透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面具,穿过历史进入21世纪?
不论是他的印刷机,还是他使用或发明的工具,例如手铸工具、铅字盒、排字角托、排字盘,都没有保留下来,只能参考后来的工具模拟再现。关于印刷场景的图像最早见于1500年前后的一幅以“死亡之舞”(Totentanz)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死亡之舞”是中世纪常见的艺术题材,表现的是死亡对生命的支配和掌控。
鉴于这样的资料情况,或许人们不应使用传记作家和历史学的惯用手段,而应当借助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这个充满谜团的人物。以这种方式走近古登堡的人,不会将其少得可怜的生平痕迹单纯地看作数据,而会将它们视为等待拼接的碎片。如此一来,有关古登堡的传说可以作为连接件代替那些未能找到的碎片,将已找到的碎片完整地组合到一起。
若想稍加了解这位发明家,甚至解开其生平中的种种谜团,唯一的可能是穿过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面具,走向美因茨城市贵族亨内·拉登;穿过他的传说故事,走向他的生活经历。
长期以来,关于这位德意志天才的传说不断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停止。在当时,古登堡这一传奇人物成为德意志身份认同的关键。在经历了觉醒的15世纪,因宗教改革和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而天翻地覆的16世纪,战争不断的17世纪,革命的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近代国家得以建立的19世纪之后,如果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能代表德意志民族身份的人物,除了图伊斯托(Thuisto)[2]、阿米纽斯(Arminius)[3]、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4],下一个这样的人物就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关于他的丰富传说甚至发展出了神话的色彩。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进入了基督教世界的现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德意志从此开始自认为是诗人和思想家、科学家和天才专家的国度。在这个留着长胡子、戴着象征市民阶层的皮毛檐帽的男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人们对于日耳曼人的刻板印象的原型,例如高效、固执和富有创造力。
然而,这个所谓的原型跟这些刻板印象一样都不是真的。直到今天都没能找到可勉强视为真实的古登堡肖像画。迄今为止,古登堡已知的最早画像出自1567年巴塞尔医学家、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潘塔莱翁(Heinrich Pantaleon)以德语出版的《德意志国家英雄录》(Teutscher Nation Heldenbuch)[6]第二卷。流行最广的古登堡画像则出自法国博物学家安德烈·泰韦的九卷本传记辞典《杰出希腊人、拉丁人和异教徒的真实画像和生平事迹,摘自其新旧绘画作品、书籍、徽章》[7]中的第三卷。只是这位法国作者与古登堡之间已相距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毋庸置疑,古登堡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这清晰地体现在传记中有关他的部分的前后几页里:在他之前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以及数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在他之后是人文主义者、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和人文主义者、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5世纪中叶前后,人们对当时刚刚诞生的印刷术的兴趣越发浓厚,我们之后将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时间。对这一创新成果的赞誉与发明的诞生是同步发生的吗?是知识水平的发展恰好导致了这项发明的出现吗?
在一封写于1454年底或1455年初,但迄今尚未找到原版的信中,当时身在罗马的西班牙枢机主教胡安·德·卡瓦哈尔(Juan de Carvajal)向他的同僚恩尼亚询问了印刷术的情况,从后者的回复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位主教对印刷术深感兴趣。至于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的消息是如何从美因茨传播到遥远的罗马,虽然美因茨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和关系错综复杂,但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消息的传播途径。
维甘德·门克勒(Wigand Menckler)自1450年起为受俸圣职候选人,1452年起担任位于美因茨附近的圣维克多修道院(St.-Viktor-Stift)学校校长。正如在《兄弟会之书》(Liber fraternitatis)[8]中可见,古登堡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5],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门克勒认识古登堡,两人之间有着联系。此外,门克勒不仅是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的幕僚,也与西班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关系密切,因此很有可能的是,门克勒将古登堡进行的工作告诉了卡瓦哈尔[9],后者又就此询问了意大利的恩尼亚。恩尼亚在1454年10月5日至31日以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法兰克福帝国议会,虽然他看到的仅是几份《圣经》五页本(Quinternio),也就是将印刷晾干的页面以五页为单位装订成本的印刷物,但这足以让这位具有影响力、人脉极广的人文主义者激动不已,他在1455年3月12日——维也纳新城举行帝国议会期间——给胡安·德·卡瓦哈尔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那个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了不起的人,写给我的内容并没有错。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圣经》,而是看到了一些以最为整洁精准的字体印刷而成的(《圣经》)不同卷书的五页本,你不戴眼镜也可以轻松阅读。我从多个可靠人士那里了解到,一共印成了158册;有些人甚至说是180册。就数字而言我不是完全肯定,但如果可以相信这些(人),我并不怀疑《圣经》已经印成。若是我早些知道你的愿望,我肯定(为你)买一册。有一些五页本是带给皇帝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试着买一本能买得到的《圣经》给你并为你付款。但我担心这行不通,既是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有人说,这些书在印成之前就有了买家。但从你让一个比珀伽索斯[6]还快的信使来通知我这一点中我可以看出,你是多么希望了解这件事。[10]
在这封信中,我们跨越数百年看到了亨内·拉登。他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古登堡,原因是他住在父母的名为古登堡的宅院里;这是他作为逃难者的临时住所,也是足以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传奇的开始。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与恩尼亚也是朋友,前者的秘书乔瓦尼·安德烈亚·迪·布西(Giovanni Andrea di Bussi)在印刷术诞生不久后就称之为“ars sacra”,即神圣的艺术,并且自己在罗马对此进行了尝试。对于意大利的大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而言,这项发明甚至成了人们生活在黄金时代的证明。德意志人则庆幸恰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成功创造了这一神圣艺术。1455年,意大利人阿斯科利的艾诺克(Enoch von Ascoli)在赫尔斯菲尔德修道院的图书馆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7]手稿并将其带回罗马,使当时的德意志人蒙羞。几乎与此同时出版的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则将德意志人的创造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大大减轻了这一屈辱。对于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仅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对这个美因茨人大加称赞。
不到30年后,被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poeta laureatus)的人文主义大学者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在其颂歌第三卷中赞美约翰内斯·古登堡道:
相信我,不逊于代达罗斯(Dädalus)或者发明了字母表的凯克洛普斯(Kekrops),出身于美因茨市民的这个人是我们名字的荣誉。他在短时间内铸造出坚固的合金字母,他教会人们用活字进行印刷。相信我,不论何时,都没有比此更有用的发明!现在意大利人终于不会再指责德意志人迟钝懒散,因为他们看到,通过我们的工艺,古罗马文学将增加好几百年的寿命。[11]
如果说罗马的帝权通过帝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8]交给了德意志皇帝,那么通过印刷术这项来自德意志的发明,德意志人不再需要意大利人,甚至可以比意大利人更快地通往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如此一来,古人的智慧和知识通过伟大的学识转移(translatio studii)直接转入德意志人之手。在这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看来,意大利人没有任何可以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媲美的成就。
策尔蒂斯将这一出色创造直接归到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中,例如将古登堡与雅典的英雄、传奇国王凯克洛普斯相提并论。传说凯克洛普斯创造了字母表;除了使用字母表和推行一夫一妻制,人们还认为他颁布了法律并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国家所属时,他选择了雅典娜。没有什么比与凯克洛普斯相提并论更加神圣庄严的了。在颂歌开头提到的代达罗斯则是手工艺者、技师和发明家的保护神。
在对古登堡的颂歌中,这位人文主义者颇有预见性地强调了文字与印刷、知识与媒介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的目的在于赞颂德意志民族的非凡创造力——感谢古登堡的发明,德意志人不用再对自诩为古罗马人后代和古代文化合法继承人的意大利人忍气吞声,也不用再对他们的成就自愧不如。策尔蒂斯将古登堡与技术大师代达洛斯、文化英雄凯克洛普斯置于同等地位,为的是强调信息与媒介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然对于这位桂冠诗人来说,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宣传帝国思想和意识形态,将祖国德意志的诞生等同于罗马帝国的再生。这样一来,因为上帝将罗马人的统治转移给了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就成为欧洲秩序的掌管者。转移体现在三个方面:帝权转移给了德意志国王,学识转移给了古登堡,艺术转移给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中世纪的大危机中,以康拉德·策尔蒂斯和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者们对建立统一帝国进行了纲领性的表述,就如人们早在但丁(Dante)[12]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13]的描述中所能看到的: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成为该帝国的秩序维护者。至于这一帝国愿景的主角,他们推崇的是在历史上被称为“最后的骑士”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更为重要的、能为他们的计划奠定基础的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天才创造。然而,他们无视德意志的现实情况,整个计划如同空中楼阁,虚无缥缈。
彼时的德意志正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则慢慢形成民族国家;除了皇帝和一些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没有人对统一帝国感兴趣——它是正在消失的中世纪的一部分,已无可挽回。但是因为这个梦想已经脱离了实际,反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其中一大体现就是对约翰内斯·古登堡的推崇,他自此完全成为德意志人的象征。最晚从策尔蒂斯这首颂歌开始,亨内·拉登成为德意志的文化英雄约翰内斯·古登堡。
在探寻这位印刷术发明者人生的过程中,如果仅因为历史发展出的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倾向就将这首来自人文主义者的颂歌置于一旁,那么就是过犹不及。与此相反,策尔蒂斯的颂歌值得仔细阅读,因为其明确指出,古登堡集技术专家和艺术家的身份于一体。正因我们对这个美因茨人的了解甚少,更应该严肃看待这位人文主义者颇具洞见的提示。在《四十二行圣经》中,古登堡的美学见地一览无遗。虽然人们经常认可和赞扬这部作品具有非比寻常的美,却很少将这种美作为创造者个人方面的证据进行解读。这本传记将对此进行尝试,将古登堡同时也视为艺术家,使“艺”(ars)这个概念的双重意义——手艺与艺术——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得以体现。
策尔蒂斯之所以将古登堡与凯克洛普斯直接进行比较,是因为后者发明了字母表,它以单个字母而非象形符号为基础,而单个字母恰恰构成了古登堡复杂创新的核心。凯克洛普斯和古登堡都以单个字母为基础,这是分析式思考方式的前提。
但为什么是古登堡呢?为什么是这个美因茨人呢?从今天的角度看,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它的出现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和逻辑,但这个逻辑恰是通过印刷术的发明才实现的。从15世纪早期的角度看,情况完全不同,否则当时就会爆发关于这一发明的竞赛,大概也会有很多人争相表示自己才是印刷术的发明者。
亨内·拉登既不是纯粹的手工艺人,也算不上学者或人文主义者。在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因阶层出身而自满的花花公子。[14]这个美因茨城市贵族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实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当时的文化科学中心——例如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帕维亚、帕多瓦或博洛尼亚,而是在美因茨这样一座当时连大学都没有的城市?康拉德·策尔蒂斯的颂歌虽然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归根结底,他的看法是不是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更加深刻?
[1] 方济各会及下文提到的多明我会、本笃会、耶稣会等均为基督教修会。修会亦作“教团”,是在修道院规则下生活的团体,其成员有纪律地工作、祈祷和研读。——译者注
[2] 神话人物。根据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记载,图伊斯托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也写作Tuisto。——译者注
[3] 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战役(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中,阿米纽斯带领日耳曼人击退罗马人,从而抵御了罗马人的入侵。塔西佗称其为“日耳曼的解放者”。——译者注
[4] 又称大阿尔伯特(约1206—1280),中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5] 基督教中未被授予圣职的成员。——译者注
[6] Pegasus,长有双翼的马,希腊神话中的奇幻生物。——译者注
[7]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日耳曼尼亚志》记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布情况,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记载日耳曼人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1455年重新被发现之前,该书遗逸已久。——译者注
[8] “帝权转移”的概念可回溯到圣哲罗姆对《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的注解:帝权从巴比伦依次转移到了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被认为是世间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永恒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用“帝权转移”的概念来巩固自身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合法性。下文的“学识转移”也类似,指文化精华从某时某地向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空间进行的线性转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