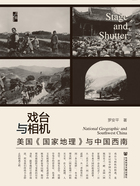
导论 戏台与相机:跨文明相遇
1909年,阳春三月,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田野。美国地质学家罗林·钱伯林一行在川西平原考察,在从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到成都的路上,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所行之处,目力所及,大地一片金黄,我们仿佛置身于万花筒般的幻象世界,这是中国的大地文化,自然天成,美轮美奂。”在灌县附近一个集镇上,一台地方戏正在上演。钱伯林悄悄爬上戏台对面的坡地拍照,但他的举动惊扰了正在看戏的人群。后来刊出的照片附有一行说明文字:“台上的演员正在卖力演出,但观众们显然对美国摄影师更感兴趣。”照片中,飞檐翘角式的戏台上,演员身影模糊,台前攒动的人群却清晰可辨:头裹包布的农民纷纷把目光从戏台上转开,扭头望向没有出现在照片里的摄影师,面露好奇,表情生动。

图1 《人口稠密的美丽四川》罗林·钱柏林摄,《国家地理》1911年12月
钱伯林的这张照片及游记刊登在1911年12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名为《人口稠密的美丽四川》。[1]钱伯林是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家,在1909年作为“东方教育考察委员会”(The 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的成员来到中国。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这篇文章,编辑加了一个副标题“探访中国不安宁的省份,当前的一场革命正发端于此”(A Visit to the Restless of Province of China,in Which the Present Revolution Began)。其时,辛亥革命正在中华大地上掀起波澜,中西方的相遇也已历经温情脉脉与硝烟战火。上述“戏台遭遇相机”的一幕,正是中西之间互视历史之一瞬。
扩展而言,不同个体、民族与国家,总是带着各自的目的“遇见”彼此,对此谁也无法否认,然而相遇之后,彼此之间是拉近了距离,还是扩大了鸿沟,却是对人类智慧的检验。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认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由于相互的差异,会产生文化的冲撞(包含征服与掠夺)和错误认同等结果,但埃科倡导另一种理念,即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原则”,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两种文化彼此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2]然而现实中,这条“理解与尊重”的道路并非坦途,反而密布着荆棘。
对全球不同文明关系的一个重要论述是“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是冲突的吗?》一文,认为当前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人们的各种反应,包括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3]三年后,亨廷顿将文章扩展为专著出版,即《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一次,标题里的问号被去掉,换为更加明确的断语: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而最主要的对立,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4]换言之,未来的危险冲突将会酿端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
亨廷顿一方面承认了世界多元文明的存在,“文明”成为复数而非单数,有助于世人以更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但另一方面,由于亨廷顿的出发点是思考如何在文明冲突中抗御其他文明,故对多元文明能否和谐共存持消极观点。纽约的双子塔被袭击倒下之后,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弥漫于美国社会中的“将他者妖魔化”等极端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受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亨廷顿“以荒谬、狭隘简化的方式凸显文明的争斗,全然忽略了人类历史上相互交流、增益与分享的一部分,”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无知的冲突”。[5]
萨义德反对文明冲突论,却并未否认文明之间的“相轻”模式。在《东方学》中,他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支配和霸权关系。东方从一个地理空间变成受现实的学术规则和潜在的帝国统治支配的领域,东方学实际是西方对自由和知识实施控制的手段,是被完全形式化并且不断复制着自身的一种方式。[6]这种后殖民主义视角的文明关系论,也受到不同学者的争议与补充,比如英国学者瓦莱丽·肯尼迪,指出萨义德在理论上的一些困境:萨义德在运用“那些历史、人文和文化研究工具”的过程中,所诉诸的正是“既产生了帝国主义又产生了东方学的那种传统工具”。[7]人类学家詹姆斯·克里福德(又译詹姆斯·克里弗德)也认为,尽管《东方学》具有挑战西方人文主义的某些特点,但是,“对于帝国话语的‘反述’,是从一个其现实已经被歪曲和否定的东方人的立场出发的。因此,显而易见,这种立场就是对立性的了”。[8]
钱柏林的照片暗示我们,中国传统地方戏曲遭遇西方的相机,无论戏曲演员怎么卖力演出,都不能吸引住观众了。在这条跨文化相遇的路上,“失语症”[9]的隐喻无所不在,正如历史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指出的,“非西方”的普通大众本应是世界历史的积极主体,但在胜者为王的书写中,却全部成为历史过程中的牺牲品与沉默的证人,造成“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二元对立的认知图式。[10]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认知图式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文明的比较研究”,他指出从最早的起源开始,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21个主要的文明单位,历史研究是为了“理解和阐释它们间的异同和关系”。[11]费孝通将如何处理这种异同和关系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2]曹顺庆认为文明之间充满异质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之间既存在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对异质性他者的观照,有助于发现文明间深层的联系,“只有在互为主观、互为他者的状况下,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自身、认识对方、和谐共处、共同发展”。[13]
时至今日,我们在跨文明相遇的路上,仍然走得跌跌撞撞、险象环生。所以,本书从一本杂志与一个地方的相遇开始,回顾那些目光与目光的交汇,思考那些曾经躲闪过的或直视过的眼神,期待它们穿越时空渡尽劫波,看见彼此,照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