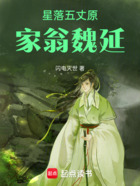
第91章 纸张,春秋
正堂中,魏正并不知道几个令史的嘀咕。
他端坐在主位上,正在身旁的董厥深入交谈。
“很久之前,宦官蔡伦就改进了造纸术。
以树皮、破麻布、旧渔网这些寻常可见的东西作为原料,造出了轻薄柔韧、价格还十分低廉的纸张。
随后,蔡伦以奏疏的形式,把改进后的纸张以及造纸工艺恭敬地献给了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看后大为赞赏,当即下诏在国内大力推行。
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
后来,左伯又对蔡伦的造纸术进行了改良,让纸张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左伯造出来的纸,洁白细腻、柔软匀密,不仅色泽光亮,书写起来更是顺滑流畅,纸质堪称绝佳,所以被叫做‘左伯纸’。
大儒蔡邕每次提笔作书,要是没有左伯纸,他都不肯轻易下笔。”
说到这里,魏正微微顿了顿,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既然左伯纸这么好用,可为何我们记账还要用这么笨重的竹简呢?”
董厥听后,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在平日里,大家写字或者写一些不太重要的信件,确实都会用纸。
但用于书写和保存朝廷官府文件、诏令的材料,依旧是以缣帛、竹简为主。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纸张目前还不能灭虫防蛀,非常容易被损坏。
而且,对于最重要的文书资料、契约合同,按照惯例,最好是铸成钟鼎和石碑,其次才是书写在竹帛上。
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保存作为凭证。”
魏正听完,忍不住讥讽道:“竹简就没有虫咬的问题了?
放的时间长了,竹简还会发霉。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从仓库里取出来,放到太阳下面去晒,麻烦得很。
再说这账目,做得乱七八糟,查起来简直要人命。
明明有纸张这么好的东西,稍稍改良一下不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董厥微微思索片刻,缓缓说道:“天不变,道亦不变。
道变,则天亦变。”
魏正听后,脸色瞬间变得冷峻起来:“这最是狗屁不通的道理。
要是一切都不变,我们现在行的还是周礼,奉的是周天子!
事物在变,难道我们还要一直守着那些陈旧的规矩,止步不前吗?”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传统守旧观念的批判,情绪也有些激动。
董厥闻言,默默闭上了嘴,不再接话。
他心中自然有诸多典故可以用来反驳魏正,比如历史上那些遵循旧制而得以稳定发展的朝代,以及变革带来混乱的例子。
但他生性沉稳内敛,不是那种喜欢与人争辩的性格。
而且在他看来,这样的魏正似乎才更像是一个年轻人。
这时,魏正也意识到了自己情绪失控,他自怀中掏出羽扇,扇了起来。
凉风扑面,大脑倒是冷静了很多。
如此仔细思量之后,倒是彻底明白过来。
魏正自穿越以来,妙计层出不穷。
先是和司马懿见招拆招,巅峰对决,最终棋胜一子,打的司马懿大败而归。
随后又和刘禅隔空对招,更是连环对策,堪称完胜。
如此一来,难免有些自矜。
现在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想大展拳脚,结果两眼一抹黑,想查账又看不懂......或者说,想看懂太苦力。
落差极大导致整个人失控。
而实际上,魏正之所以能够大败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完胜刘禅,并不是他真的很厉害,而是他拥有先知这个金手指。
很多事情上,可以从结果去反推,很多事情的脉络就清晰多了。
现在到了县城上去治理,金手指的功能自然就被削弱了不少。
“龚袭啊,很多人,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利益,根本就不会去思考改变。”
冷静下来之后,魏正的话都自信了很多,他习惯性的起身,走起了四方步。
“蔡伦发明蔡侯纸,那是为了讨好邓太后,为了做官。
而左伯改良纸,纯粹是因为他热爱写字。
因为有这种追求,所以他们对原有事物进行改良,创新也就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可现在呢,大家宁愿守着这些又笨又麻烦的竹简,也不愿意尝试去改进,去利用更好的东西。
长此以往,我们又怎么能进步呢?”
董厥听了魏正这番话,心中已然有了大致的方向,不过还是试探性地说道:“君侯的意思吾明白,如今账目记录在竹简上,太过繁重,查账也极为不便。
依君所言,我们不妨着手改良纸张,而后让官吏们把账目记录在纸张上,如此一来,既能减轻重量,也便于整理和查阅。”
“正是这个道理!”魏正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蔡伦不过是个宦官,左伯也只是一介儒士,他们都能改良纸张。
而我们身为朝廷命官,手底下掌管着大量的匠工,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为何就不能改良纸张,让它变得更加坚韧耐用,同时还能防虫防蛀呢?
只要我们肯用心去做,必然能成功。”
魏正说到这里微微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不过话说回来,无论竹简也好,纸张也罢,它们都只是记录的载体。
真正重要的,是记账的方式。
现在这账目做得太过复杂繁琐,只有专业的账房先生才能勉强看懂,这怎么行呢?
我们必须把记账的方式简化,要让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看得明白账目上的收支情况。
这样一来,不仅便于我们管理,也能方便对账目来往进行监督。
避免一些上计所谓的春秋笔法。”
听到这里,董厥的眉头微微皱起,心思开始快速运转。
作为令史出身,他很清楚,一旦账目变得通俗易懂,那些原本依靠复杂账目浑水摸鱼的人可就没了操作空间。
要是君侯能轻松看懂账目,那各个曹里养的这么多擅长算账、管理账目的掾属,作用可就大打折扣了。
而且,各地的世家豪强,平日里没少在账目往来里做手脚,趁机中饱私囊。
往后账目一清二楚,他们再想干这些勾当可就难如登天。
这一变革,无疑会触动一大批人的利益。
但董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他出身南阳义阳,宗族的大部分力量和资源都在南阳,在曹魏那边。
至于自己,在大汉的南乡县任职,根基不深。
在益州的资源和宗族力量更是十分有限。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势单力孤,能插手的事务范围也较为狭窄,获得的利益也很少。
实际上,对于董厥这样近似流寓过来的官员而言,仕途的发展才是重中之重。
只有官职越做越大,在任时间足够长,才能谋取更多的好处。
从而在家族族谱上再开一支,光宗耀祖,为自己和家族赢得更高的地位和声誉。
而魏正推行的这些改革,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得罪的大都是本地人。
从长远来看,若是成功了,无疑是大功一件,自己作为坚定的支持者,必定能从中受益,仕途也会更加顺畅。
至于不能中饱私囊这件事,那些在本地根基深厚、拥有大量资源的益州人,才是最受影响的。
他们长期以来依赖着旧有的体制谋取私利,这次改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切肤之痛。
最重要的是,南乡县,可是魏正的封地!
想到这里,董厥心中暗自念叨:死道友不死贫道。
表面上则是一脸凝重的俯身过去,道:“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