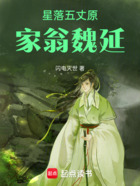
第74章 祭祀,马超
定军山北,雷公山脚下,一片静谧而肃穆的氛围。
这里距离汉水北岸约二里,坐落着大汉骠骑将军马公超之墓。
数千将士整齐列于墓前,他们身着素衣,神情凝重,在微风中,衣袂轻轻飘动。
为首的,正是大汉假相胡济,其身姿挺拔,神色沉痛。
前军师魏延和长史杨仪分列两侧。
接下来,各个将领依序站立,皆面容严肃,眼神中或多或少带着一丝哀伤。
众人望着马超的墓,面色悲戚。
然而,这悲戚之中,真正发自内心的,或许只有马岱和吴班。
马岱站在墓前,眼中泪光闪烁,心中满是对兄长的怀念,同时也深深感念丞相府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兄长马超。
而吴班,刚刚经历兄长吴懿的惨死,此刻站在此处,心中五味杂陈,悲痛难掩。
他虽向来以豪侠著称,但形势之下,已经不允许他放纵自己的脾性。
吴班虽然不是宗家,但也相距不远。
他的父亲吴匡更是亲身参与那一场巨大的宫廷动乱。
宗家是吴懿的父亲,早在刘焉当益州牧的时候,就携家带口而来。
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下,吴班虽然更喜欢军事,但对政治斗争也有着清晰的认知。
胡济魏延等人此番行动,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谋反。
更不是想与刘禅撕破脸。
杀他兄长吴懿,更多的是一种警示,是对刘禅以及吴家此前参与诛杀刘琰一事的强硬回应。
这是一场双方势力在权力棋盘上的激烈博弈。
吴班心中清楚,如果硬要凭借那股豪侠的血性,与胡济和魏延等人硬刚到底。
那局面将彻底失控,陷入不死不休的惨烈境地。
一旦走到那一步,即便胡济和魏延依旧选择拥立刘禅,继续维持蜀汉表面的统治秩序。
但为了彻底消除后患,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其他心怀异志者彰显他们的决心与手段,必然会对吴家展开残酷的清洗,将吴家斩尽杀绝。
吴班想到吴家满门老小,想到了为了家族连番牺牲的族妹,想到那些无辜的生命,心中便是一阵阵的绞痛。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冲动,让整个家族遭受灭顶之灾。
豪侠之气固然重要,但此刻,家族的存亡、众多亲人的性命,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兄长吴懿被杀之后,吴家的领头人,这一沉甸甸的负担,就已经压到了他的肩膀上。
吴班最终还是咬了咬牙,做出了那个艰难的决定——投降。
尽管这个决定让他满心屈辱,觉得背叛了兄长吴懿,可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别无选择。
如此才能给吴家留下一丝生机。
“七年前,丞相上表北伐曹魏,途经马公超墓,特意令其弟马讳岱挂孝,且亲自诣墓致祭。”
胡济的声音低沉而庄重,“转瞬之间,七年已然过去。
如今丞相也已长眠于定军山下。
先帝遗志和丞相的宏愿尚未达成,我们却已失去了主心骨。”
“马公超一生,驰骋疆场,为大汉立下赫赫战功。
丞相敬重他的忠勇,当年那一场祭祀,是对英雄的缅怀,更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激励。
丞相用一生践行着兴复汉室的誓言,他的勤勉、他的智慧、他的担当,都是我们前行的方向。
北伐之路,道阻且长,可我们绝不能因为丞相的离去就停下脚步!”
胡济的声音逐渐激昂起来。“将士们!
丞相虽逝,但北伐大业不能停!
马公的热血,丞相的遗志,都需要我们来传承。
我们要带着他们的期望,踏破曹魏的防线,光复大汉的山河!
我们回家!”
众将士被胡济的话语所感染,纷纷握紧手中的兵器,齐声高呼:“北伐!北伐!兴复汉室!”
声音如滚滚雷鸣,响彻在雷公山脚下,久久回荡。
当声音停下之后,胡济看向了魏正,接着大声道:“请大汉征西大将军魏公延之子魏正忠贤,为马公超诵祭文。”
闻声,早有准备的魏正,迈着沉稳的步伐,从容地走到了众人前方。
此次前来祭祀马超,其背后深意不言而喻,正是为了拉拢降将之心。
毕竟,无论是马岱,还是姜维等人,皆来自凉州,属于归降之士。
唯有将他们的地位予以拔高,让他们感受到重视,方能激发他们的斗志,使其更加全力以赴地为大汉效力,一心只为打回关中、收复凉州。
虽说祭祀马超看似只是表面功夫,然而能想到去做,且愿意投入精力,便足以彰显诚意。
而这一建议,正是魏正提出的。
他不仅如此谋划,还提议后续不仅要祭祀,更要为马超修建庙宇。
当然,考虑到诸多因素,此事需暂且延后,要安排在给丞相诸葛亮建庙之后。
在这个时代,帝王的观念里,立庙绝非一件简单之事,它象征着等级森严的礼制,关乎着朝廷的威严与秩序。
就如历史上,刘禅直至 263年,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掌控朝政大权且屡次恳请之下,才最终为诸葛亮立庙。
但在魏正看来,祭祀和立庙无疑是不花钱却能办大事的绝佳典范,何乐而不为呢?
故而,在他的提议下,胡济率领所有将领,以及数千将士,浩浩荡荡地前来祭祀马超。
至于人力......这个时候的人力需要花钱么?
但是,令魏正心中疑惑的是。
在胡济和魏延一番密议之后,竟执意要求他来朗读祭文。
并且这份祭文,还需由他魏正亲自撰写。
仔细忖度了好久,觉得其中不可能有坑的魏正,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委托。
此刻,环顾四周,魏正清了清嗓子之后,便开始大声朗读起来:“岁在甲寅,季秋之序,金风萧瑟,丹枫飘坠。
吾等恭临汉骠骑将军马公超灵前,敬备香烛醴酒、珍馐庶品,以祭英灵,悼词曰:公起西凉,幼负逸才,勇冠三军......
汉室陵夷,奸佞弄权,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公虽居边徼,然心怀天下,目睹社稷丘墟,哀民生之多艰,遂怀壮志......
时曹贼擅权,荼毒中原,公为保阖家、护宗祊,秉持大义,奋袂而起,欲殄灭曹贼,兴复汉室。
讵料曹贼狡黠诡谲,竟执公之父母、宗族及妻孥为人质......
公痛彻心腑,然不为所动,深知屈膝则负家国,辱正义。
曹贼怒而屠戮公之亲眷,噩耗骤至,公如遭雷霆,肝肠寸断。此岂公之本意?
实乃为家国大义,万不得已之举。
公矢志报国,竟累及至亲,其痛何堪,天地同悲!
公虽困厄缠身,犹振拔而起。辗转至蜀,幸遇昭烈帝......后随先主进取益州,攻城略地,勋绩卓著,实乃大汉之擎天之柱。
公勇若虓虎......为后世所仰。
秋风瑟瑟,落叶翩翩,吾等追思公之德,缅怀公之功,公之精神,永垂不朽。
愿公之灵,永安泉壤。亦望后昆,以公为范,胸怀家国,奋然前行,复兴家国之盛业。尚飨!”
魏正的这一篇祭文,充满了对马超的同情。
虽然从后世历史的角度上看,马超简直是个丧门星,连累宗族妻儿。
甚至有人说他是个无父无母无君无义的烂人。
但魏正觉得,如果马超知道这些事情的结果,或许并不会这么做,他只是玩砸了,而不是成心想害死家人。
退一万步来说,现在毕竟是祭祀马超,是在拉拢马超的家眷,拉拢马岱和他们的部曲。
所以,行文之中,自然要多多为马超开脱。
或者说,站在马超的角度来说话。
一篇慷慨激昂祭文读完,马超的家眷们早已泣不成声。
就连马岱,也是虎目含泪,他身边的羌胡义从,心潮澎湃,哀声一时传染出啊去,三军尽皆垂泣。
数千人身着白色的素衣,齐声痛哭,哀伤的气氛下,魏正也是热泪盈眶。
擦眼之际,目光落到马超的家眷群中。
只见一名年轻女子哭得尤为伤心,她的双肩不住地颤抖,胸口难以抑制地剧烈起伏着,仿佛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无尽的痛苦。
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断滚落,打湿了身前的衣衫。
只这一眼之间,好似被什么触动,魏正不禁泛起怜悯。
因为在这哀伤的氛围中,只有她的悲痛如此真切,如此真实,如此的令人动容。
......
李福踏入宣室,目光一扫,见刘禅与蒋琬安然在座,心中彻底明白。
陛下这是已然选择了留守京城的蒋琬携手合作。
当然,当李邈要被下狱诛杀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他们益州势力暂时还没有上桌的资格。
李福毫不犹豫,当即双膝跪地,身子前倾,伏地而拜,恭恭敬敬地向刘禅行了大礼,口中高呼:“陛下万安。”
蒋琬见李福如此,神色依旧平静如常,仿若一切尽在他的预料之中。
刘禅微微抬眼,目光落在李福身上,神色略显威严,开口问道:“尚书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李福恭敬地抬起头,脸上带着几分郑重,缓缓说道:“启禀陛下,前些时日,丞相身染重病,臣奉陛下诏令,亲赴丞相营帐,问询国家未来大计。
丞相彼时虽身体抱恙,却心系陛下与大汉江山,提及陛下所问之事,丞相深思后曾坦言,公琰(蒋琬)正是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合适人选。”
闻言,刘禅会心一笑。
李福,是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