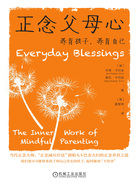
同理心
在解开拉格妮尔小姐所中魔咒的过程中,高文爵士的同理心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从她的眼中瞥见了丑陋外表之下的美,尽管那份美是隐藏着的,但依旧存在于那里。“……在她那可怜的骄傲和她那丑陋的头抬起来的样子,让他想起了一只被猎犬包围的鹿,而她那昏暗的眼神深处仿佛藏着求救的呼唤。”
城堡里的狗象征着同理心,这令人类感到羞愧。“只有猎犬卡波尔走到她跟前,用温湿的舌头舔舐着她的手,用琥珀色的眼睛望着她的脸,完全无视她的丑陋。”通常,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发现狗和猫可以教会我们什么是自主权、同理心和接纳。可能这就是我们与它们共处的原因。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基础课程。养育孩子则是高级课程。无论是否准备妥当,我们都已注册。可是又有谁真正准备妥当了呢?
*
反思我们在生活中的同理心时,这样问问自己可能会有些帮助:“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最想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不妨花些时间来反思,然后看看有哪些词或图像进入我们的头脑……
很多人最渴望的是在家里被看到,被接纳,被待以善意、同情、理解和尊重,获得自由、安全、隐私及归属感。这一切都有赖于父母的共情能力。在孩子受伤时,共情是容易的;但在他又踢又叫扔东西时,就要困难得多。当他的兴趣或观点与我们的相冲突时,保持同理心也是困难的。我们需要有意地去培养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状况中保持同理心的能力。
在培育同理心时,我们要试图从孩子的立场来看待事物,并试着去理解他可能产生的感受或体验。我们尝试把一种同情的觉知融入每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中,这也包括我们对自身情感的觉察。
对一个新生儿的同理心是什么样的呢?想象他来到这个与九个月前全然不同的世界上时会感受到什么。不妨从对子宫的想象开始,温暖、湿润、安全,有节奏的声音,一种被包容、被抱持、被摇晃的感觉……那是一种浑然一体、与一切都没有区分的体验,什么都不缺少,什么都没有丢失。
我们可以从一名19岁的年轻人在母亲节写给母亲的信中瞥见这个触动人心的世界:
衷心祝愿你拥有充裕的平静和力量。感谢9个月甜美的冥想。在羊水中,我如鱼儿一般呼吸。当食物如此纯净时,既用不上嘴,也用不上喉咙……祝福。
在出生之际,我们离开了这个和谐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崭新且全然不同的世界里。那里可能有着刺眼的光线和寒冷的空气。我们可能会听到突如其来的噪声,感觉到皮肤挨着粗糙或坚硬的物品。我们第一次感到饥饿。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陌生而纯粹的体验,没有对任何事情的了知作为滤网。想象一下,你被猛然推入这个陌生的环境,你全然仰赖这个家庭对你语言的理解能力、对你整个人和敏感需求做出反应的能力。
为什么把婴儿当成能够全然感受、全然体验的存在,对我们而言会这么困难?为什么我们完全无法漠视朋友、爱人甚至是陌生人的哭泣,却可以让婴儿哭个够?当我们和孩子保持距离时,我们可能在抵抗什么或者逃避什么?
我们有可能是在保护自己,以免承担更多工作。每时每刻都积极响应的养育方式在短时期内确实是更大强度的劳作。关注一个孩子的肢体语言,尝试不同的事物,保持敏感以免回应不足或回应过度,拥抱,安慰,轻声吟唱,这一切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更多时候,他们会打断我们的睡眠,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当孩子的需求与我们的需求一致时,我们自然比较容易对他们抱有同理心。真正的考验发生在他们的需求与我们的需求相冲突时。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同理心,也可能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以免回溯年幼时自己的身心需求未能被回应的痛苦。对孩子的脆弱感同身受可能会让我们痛苦地想起自身的脆弱。
作为成人,若要回避承认年幼时的痛苦,方法之一就是转向婴儿时期所依赖的应对机制。在一个没有响应的环境中,很多婴儿会在情感上封闭、退缩。如果这是在年幼时学会的应对痛苦、困惑的方法,在成年后我们就可能会继续这样做,以完全自动、毫无觉知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忽视或贬低(而非关注)婴儿和自己的感受,并以“小孩子挺皮实的,他会适应的”“哭不会伤害到他的”“我们不想宠坏他”为理由。接着,我们可能会试着借助食物、酒精、药物、电视、电子设备或者报纸,让自己平静下来,把痛苦抛在脑后。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拥有强大的内在资源,它们远胜于这些用来逃避的工具。在这些时刻,关注内在并带着同理心去联结,是一种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更令人满意的健康方式。哪怕我们在年幼时未能学会,只要我们准备好听取灵魂最深处的呼唤,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帮助我们从灵魂的最深处唤醒这种最原始的能力。
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让母亲故意对婴儿反应过度或过少,而不是以一种谐调的、富有同理心的方式来匹配他们的感觉,婴儿会立即表现出气馁和忧伤。在《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有关于这些研究的报道。
父母和孩子之间长期缺乏谐调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对于孩子某些特定的情感,如快乐、眼泪、被搂抱的需要,倘若父母持续无法表现出同理心,那么,孩子会开始回避表达,甚至回避去体验这些情感。由此推测,在孩子的亲密关系中,这些情感会被渐渐消除,尤其是在孩提时期就被或隐秘或明显地持续抑制的情感。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
《情商》
这些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戈尔曼引用了精神病学研究者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的观点:在父母与孩子之间,那些微小、重复的交流形成了情感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因此,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建立联结的舞蹈中,对孩子成为完整的个体、增强情绪能力、拥有自主权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哭了十分钟后不再哭泣终于入睡的“乖”婴儿,可能是一个学会了放弃的婴儿。然而放弃是我们想要教会孩子的东西吗?我们想要孩子发展出来的“独立”就是对需求不被满足的适应吗?情感上的封闭、失去部分的活力和开放性,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吗?其实,我们真正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他们的感受是重要的,我们会予以回应,他们可以信任和信赖对他们很敏感的人,他们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并表达自己的需求,与他人相互依存,这些都是被允许且安全的。
*
当婴儿开始蹒跚学步、探索世界时,他们对身边的所有事物都怀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和愉悦。与此同时,当他们试图去做那些力所不能及之事,被尚未拥有某些技能所局限时,这个世界也为他们设下了很多挫折。因而,他们在不断向外探险时,依旧需要回到一个和他们情感亲近的慈爱之人身边。学步期的幼儿依靠的正是父母的敏感和理解,父母以此创造一个环境(如果是在托儿所的话,就去选择一个环境)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安全地探索和发现,同时给他们适当的限制和界限,提供他们所需的温暖和安全,比如将他们抱在腿上或者搂在臂弯里。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同理心的表达形式不再全是躯体性的了,尽管有时他最需要的是一个沉默的拥抱,或者让我们握住他的手。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得到的提示可能令人困惑,难以理解:前一天,(甚至前一分钟)他们可能还很友好,乐意沟通,但第二天,他们就可能会愤怒,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与孩子沟通的能力,甚至是沟通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对他们持久而郑重的承诺,哪怕他们可能对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怀有疑虑,或者拒绝我们的示好或询问。
在拒绝面前保持同理心,这要求我们不要让受伤害的感觉妨碍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可能正在遭受的痛苦或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无论被多么可憎的(就我们的想法而言)咒语所控制,无论披上多么黑暗的伪装,孩子都需要感觉到我们与他们联结在一起。这份正念的坚持并非出于控制欲,也并非要强留孩子,或是出于对孩子的依赖而纠缠不休,而是出于对他们的承诺——我们会适时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自己并非孑然一身,我们并没有忽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失落、忧伤,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感受到亲近之人依旧是同盟,依旧能够理解和爱我们本身,这是多大的帮助!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吗?所以,作为父母,持续地重建和修复与孩子的关系是我们的天职。这需要时间、关注和承诺。如果我们持久地缺席,或身体在场却心不在焉,孩子就不可能感觉到信任与亲近,就不可能让我们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孩子们有一种切入问题要害的奇妙能力。有个朋友为我讲了一个故事。某个晚上,她陪着八岁的女儿就寝。她的女儿对抢劫者和绑架者充满强烈的恐惧。连着几年,这份恐惧都会在晚间出现。母亲坐在床上聆听,内心挣扎不已,既想安慰孩子没什么可怕的,又明白在女儿所面对的最深、最持久的恐惧面前,理性显得苍白无力。
她换了一个策略:告诉女儿她在这个年纪时也非常害怕夜晚。年幼的女孩严肃地看着母亲,问道:“你也怕?”她点头称是。女儿沉思片刻,极其认真地问:“那你能告诉你的妈妈吗?”她的母亲停顿了一下,回想着她的孩提时代,说:“不,我没能。”
在八岁这个年龄,她的女儿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了解到,与亲近之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是多么重要。她知道父母那份开放、接纳和深具同理心的全然临在是何种模样。她的恐惧不曾遭到忽视、嘲笑或贬抑。在被最真实的恐惧掌控时,毫无疑问,她感觉到了足够的安全,可以告诉母亲,而无须独自面对恐惧。
当孩子与我们分享痛苦时,作为父母,如果将正念融入那时涌现的想法和情感中,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能观察到我们因某种情感而生发的不适,以及我们内心可能产生的任何想要平息、消除或贬抑某些疑虑和恐惧的冲动,我们就有机会改善自动反应行为,成为更具同理心、更支持孩子的父母。
有时候,当我们被要求倾听、保有同理心、以体贴的方式回应时,可能会发现自身的强烈情感与反应会压垮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需要来照顾我们,而不是被我们所关照。
当我们发现自己正朝着偏离原意的岔路行进时,倘若能够把正念带入这些时刻,就可能看清正在发生什么,可以选择停下来甚或转头重新开辟一条更理性、更具同理心的道路,这种时时刻刻的敏感提醒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时刻去分享自己的情感,知道何时分享是没有必要甚至具有破坏性的。通过对内在声音的倾听,我们可以学会何时该伸手相助,何时该顺其自然,何时该说话,何时该保持沉默,以及如何在沉默中临在,让他人感觉到我们富有同理心的临在,而不是拒绝和退缩。没有人能够教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从经验中学习,从每一个接收到的线索和提示中学习,并学着去关注它们来来去去时自己的心理状态。
当然,这并不容易,在特别令人不安和存在冲突的时刻,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情绪化,说出一些日后令自己后悔的话,或者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这些“破裂”,即疏远和断开联结的时刻,在任何关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孩子也需要经历这些——他们的父母也是人,有时可能会不敏感、不适应,甚至因为缺乏同理心而焦躁和愤怒。在这种压力和破裂的时刻,以及在重要的修复和恢复过程中,人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正如家庭治疗师丹尼尔·休斯在他的《以依恋为中心的家庭治疗》(Attachment-Focused Family Therapy)一书中所指出的,亲子关系的力量,有时被称为安全依恋,是以这种破裂后又修复的动荡过程,以及亲密和安全的感觉为基础的。在这样的时刻,父母和孩子可以产生一种感觉,即他们可以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和经历事情,但在充满爱和值得信赖的关系中,这样做是安全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关系得到了改善,对于孩子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自主感和联结感也得到了加强。
怀着同理心不断编织并重建与孩子的联结,是正念养育的基础。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可以指导我们做出决定,并帮助我们把握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联结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