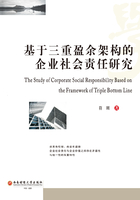
第二节 国内研究动态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思想最早可追溯到Clark的《改变中的经济责任基础》一文,Clark(1916)认为研究社会责任的观点中很大部分内容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但却往往被大家忽略了。自从这一观点被提出后,理论界就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未中断,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于1924年被谢尔顿第一次提出,之后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而相对于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我国则起步较晚。虽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及相近的讨论在我国近代甚至古代的文献古籍中都能够找到,例如儒家的“义利之争”、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兼爱、节用、利民”等都蕴含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但是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是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而产生,我国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企业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后才开始的。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关注,可参见1990年我国著名学者袁家方在其著作《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论述:“在生产经营中,企业不但要考虑本企业的利益,还必须考虑社会诸方面的利益,考虑到社区、消费者、相关企业、社会整体以及国家的利益。因此,企业不仅应具有经济的观念,还应具有社会的观念、宏观经济发展的观念、公众利益的观念乃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观念。”这一探索引起了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并将企业的相关群体纳入研究。由此可见,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出现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地被拓展。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我国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袁家方(1990)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大小贡献之说,小的方面则是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本身的发展有利,往大的方面说则是大利,对国家和社会有利。刘俊海(1999)认为企业除了对股东负有责任之外,对公司员工、债权人、客户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等和社区环境都负有责任,应关注所有利益者的责任。屈晓华(2003)从企业规章制度方面出发也同意以上观点;宋红霞(2014)在研究公司风险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也用到了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且同意企业应该履行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政府和社区(慈善、捐赠和环境等方面)的责任。1999年,我国学者刘俊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公司在为股东牟取利润之外,还需尽可能地增加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债权人利益、员工利益、客户利益、生态环境利益及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等。
卢代富(2001)结合我国国情,批判了国外学者提出的“自愿观”和“经济牺牲观”等社会责任观点。他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创造价值过程中,除了要保护股东权益,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群体的责任。喻勤娅和吴勇敏(2004)认为不同阶段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有所不同,企业应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能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群体和社会进行补偿,从而确保企业顺利发展。李冬生和杨秋林(2006)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责任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细化,认为企业所缴纳的各项税费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利益,并对社会产生影响,故应列入社会责任范围。2008年,刘兆峰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2012年,林波、殷格非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定义,即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责任”,即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企业活动中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中的一种构想。他们还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认为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李淑英(2007)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两方面定义了社会责任,她强调企业应超越单纯追求利润这一经济目标层次,把目光更长远地放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人的价值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上。高红贵(2010)提出了社会责任仅考虑利益相关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融入环境因素,提出了“生态经济社会人”假说,他认为社会责任不仅要对利益相关群体负责,更要对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环境负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引进绿色环保设备并进行安全生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已出现的污染问题,企业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配合治理,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确保企业、社会和环境三者能和谐健康地可持续发展。企业不能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积极承担对债权人、顾客、员工、供应商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王立满,2016)。
可见,学者们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说法不一,但都认同企业在经营中除了追求股东利益也应考虑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这一说法(李月晓,2016)。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打破了传统股东利益至上观点,其认为公司目标是实现“权益、负债以及所有其他公司在外的可能的索取权的市场价值之和”最大化,即不局限于单一的利润目标,在自身与利益相关者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求利益平衡。企业在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各个主要利害关系群体,主动承担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及责任范围体现出社会责任的多维性,这为我们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提供了方向与思路。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在继承了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观点”和布鲁曼的“企业四责任说”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互相对峙的“综合观”和“独立观”。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公司社会责任的“独立观”者主张,公司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会使其经营迷失方向,增加经营成本,不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保持竞争地位。弗里德曼斥责公司社会责任学说为“一种自由社会里根本的破坏主义”,认为“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就是在不违背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其资源,并致力于设计完备的、能够增加公司利润的活动。”而“综合观”认为利润最大化仅仅是公司目标之一,除此之外,公司尚应以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目标。各种企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必须在企业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者之间维持平衡。前者集中体现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后者体现公司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即社会公众的义务。
通过整理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的研究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同卡罗尔的“综合观”。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西南政法大学卢代富教授(2002)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一书中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以外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即除股东以外,企业还应该承担起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其中该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仲大军,2002)。
屈晓华(2003)从制度和行为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了诠释,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了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和市场的友善,是企业经营的综合目标,它主要体现在企业通过政策制度和相应的行为来表达对员工、顾客、供应商、商业竞争者、社区、环境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责任,具体来说这些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生态责任、伦理责任等。
企业社会责任著名研究学者黎友焕(2007)则对企业社会责任作了一个相对完整和动态的定义:“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即企业应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企业活动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林波、殷格非,2012)。
此外,我国出台的许多政策法规也都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阐述,如2006年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的第三条,其同样认为上市公司应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积极保护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积极从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从而促进公司本身与全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又如,2014年“全球企业社会责任领袖峰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楚序平说,国资委将支持企业履行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ISO26000作为国际社会责任指南,第一次在全球统一了社会责任的定义。ISO26000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企业需要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具体包括了以下六个方面:①企业应承担其决策和活动对环境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责任;②企业的行为应公开透明且符合道德要求;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支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表现;④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充分重视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⑤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和准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⑥企业社会责任应融入企业的运营与管理工作中。
本书也同样认同企业的“综合观”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作为社会上的重要经济主体,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肩负着维护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即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及环境等紧密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进而实现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
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
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先建立一套指标体系,然后进行实证检验。另外,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对企业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企业的经济责任层面,而对环境和社会责任层面则不加以考虑。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大量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和指南逐步涌入中国,我国政府、有关行业组织和企业以及学者们都对企业社会责任给予了高度重视,也开始纷纷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进行积极探索。
企业社会责任是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李立清(2006)以此为出发点,参照国际较为流行的SA8000建立了一套具体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人权保障、劳工权益、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五个方面,建立了13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这套指标结合SA8000将劳工权益及人权保障方面设计得很全面,但由于其认为社会责任不包含经济和法律责任,所以在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对社区政府责任等方面的设计明显薄弱,没有全面涵盖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国情。熊永清等(2008)选取15个财务指标,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型,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初始信息的权重,并以深交所制造业16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周旭卉(2009)基于社会责任评价的金字塔理论,以深交所颁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为参照,构建了一套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宋建波和盛春艳(2009)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包括投资者、雇员、消费者、商业合作伙伴、政府、社区及公共事业、环境等)构建了指标体系,最后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的数据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应用。刘恩专(1999)在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中指出跨国公司应当承担技术知识传播、人力资源、经济安全与稳定、环境质量四方面的责任。杜中臣(2005)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广义地分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探讨了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不同方式,得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快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结论。杜讳和穆涌(2009)利用外部结构资本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包括消费者、商业合作伙伴、政府、社区这四个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贺正楚(2011)以低碳经济为视角,归纳总结了包括电力供应、经济法规、环保节能和社会和谐四大指标的社会责任内容。牛振华(2011)以传统企业评价为基础,建立了运营管理能力、资产经营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市场管控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六大指标。张涛和李丽娜(2012)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生态责任、伦理责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模糊综合评价。晃里等(2012)从企业员工视角,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以及环境责任三个方面。阳秋林和付柏桥(2012)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基础,提出了社会责任应该包括财务责任、环境责任、资源责任、员工责任以及社会贡献五项。陈红岩等(2012)以ISO26000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煤炭业特点,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体系中包含了六个方面,主要内容涉及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以及社区问题等。朱永明和许锦锦(2013)研究了国有企业,提出了应该从九个方面对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分别是:市场责任、经济责任、公益责任、环境保护责任、文化责任、法律责任、质量保障责任、劳工权益责任和创新责任。赵勍升(2008)在讨论零售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将社会责任分为核心责任(包括对顾客、股东和员工负责)、中间责任(包括对供应商、配送商、金融机构和社区公众负责)以及外延责任(包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三部分内容。张明泉和陈佳婧(2008)针对石油行业建立了包括非经济责任、经济责任、员工责任、社区责任、生态环境责任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谭中明和陈渊(2009)研究了保险行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并参考SA8000标准构建了经济、法律、伦理以及慈善四大社会责任评价指标。李名宏(2001)在电信企业社会责任探讨中将电信行业社会责任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三大类别,并探讨了如何树立社会责任观念问题。孙召亮和汪冬梅(2011)将房地产业分为政府责任、股东责任、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员工、社会公益七个维度,并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了评价研究。蒋艳和阳秋林(2012)研究了我国的核电行业,归纳总结出社会责任的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非经济责任、社区责任、生态环境责任、经济责任以及员工责任。汪大海(2012)在慈善视角下构建了本地化战略、环境保护、社区建设、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五大社会责任因素。
随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深入,实务界也开展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的建立。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等都对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进行过研究,比如2005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制定的我国第一个行业性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提出了纺织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标体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评价体系与标准》中,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维度;2008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提出了包括经济绩效、能源、安全保障以及环保等内容在内的80多项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这些指标的建立都存在一种主要的方向,即尽量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力争全面满足其要求,注重与国外标准的契合度,但从社会责任实践的角度看,这些评价体系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我国社会责任建设的需求。
三、三重盈余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
三重底线理论(the triple bottom line theory)于2000年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出版的论文期刊中,该期刊文献是我国学者翻译的一篇外文文献,虽然文章没有对三重底线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但是,文章中倡导的企业清洁生产、关注环境的生态效益、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是三重底线理论的思想基础(波尔·华利德,200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后我国学者在实践领域积极地推进了三重底线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往往只注重对经济绩效的评价而忽视了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难以体现对“三重绩效”的和谐性要求。从评价的方式上来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一直都是以财务指标为主;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呈现出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2002)、《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2006)等。虽然这些绩效指标评价体系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经济利益导向”的评价模式,但仍然与科学发展观和“三重绩效”理论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使得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温素彬(2009)在对比了当前全球最具代表性的4种社会责任报告模式之后,提出全球报告倡议是最合理并且易于执行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化的发展浪潮中获得竞争力,其企业报告模式必然会向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方面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即全球报告倡议的报告模式发展。现代企业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生态经济实体。生态环境系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基础(方拥军,2010)。当今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不再单单停留在经济责任的传统意义上,更多的是要求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会增加企业成本,但也能提升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从而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李丽娟,2011)。但是我国企业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企业的“三重盈余”,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对立性。那我们就应该在矛盾的关系中寻找三者的最合拍点(Andrew W. Savitz, 2013)。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仍然是将追求经济绩效作为首位,并且社会对企业“三重底线”的管理力度也不够,政府只对严重影响环境和社会的企业予以惩罚。如果我国企业要想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要看清眼前的形势,摆脱竞争劣势,更新发展理念,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业绩(彭海珍等,2003)。
纵观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虽经历了多次调整,却仍然没有涉及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出现了平衡记分卡(Kaplan, 1992)、EUA评价系统、绩效三棱柱(Neely, 2002)等一系列新的绩效评价体系,但是也不能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企业绩效进行全面评价。结合当今和谐社会对我国企业绩效评价的新要求,我国企业绩效评价应向构建“三重盈余”和谐绩效评价体系的方向发展(赵喜仓、周曼,2007)。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和已有的研究基础,三重盈余评价模型得以不断创新,构建的基于权变理论的企业三重绩效综合评价模型,也能够增强绩效评价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决策相关性(温素彬,2010)。就当前我国国情而言,应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G3版指南指标中理性选择适合我国的指标,不断完善企业“三重底线”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三重底线”指标,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企业“三重底线”指标的评价(谢良安,2009)。
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了企业三重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比如由静态绩效评价、静态平衡性评价、动态协调性评价所构成的结合了静态绩效和动态绩效的企业三重绩效评价模型(温素彬、薛恒,2005)。“三重盈余”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衡量和评价与企业经济因素表现相对应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表现(赵佳荣,2010)。利用“三重盈余”框架,可采用层次分析法构成基于“三重盈余”绩效模式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框架(宋荆、顾平、席娜利,2006)。不过,虽然“三重盈余”评价模型从本质上反映了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关系,突破了传统业绩评价模式所反映的单一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此评价方法难以操作(麻晓艳,2007),不能灵活地运用于各个行业始终是个问题。林则毅和于悦(2008)将“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指标与平衡记分卡模型指标相结合,使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相关因素成为平衡记分卡模型指标体系的一部分,形成一个新的评价模式,该模式从战略全局上考虑了企业的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结合平衡记分卡对企业经济绩效的科学评价,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企业综合业绩的度量与考核,让三重盈余评价模式能够更广泛地运用到各行各业中。
不难看出,三重盈余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已经日趋成熟,研究已从最初单纯的理论分析,到选择和划分“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中的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所包含的具体指标。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企业效益必须要从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环境层面,不仅要计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而且还要计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赵佳荣,2010),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三方面的平衡发展,并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开始对其构建“三重盈余”评价模式,特别是资源型的行业,运用“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来评价企业绩效更是当务之急。
四、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挑战,要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大多数公司都想成为模范企业公民,即除了追求股东的利益之外,也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但问题在于,对股东利益的追求可以使公司在付出成本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必然产生费用,这也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吗?如果能产生经济绩效,企业肯定存在积极的“投资”行为,但如果不能带来更多的效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因此,公司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与公司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的关系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构成了现代公司伦理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杨自业、尹开国,2009)。Griffin(2000)也指出,公司社会绩效问题是“21世纪的研究方向”。
自Friedman(1962、1970)提出“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获取利润”以来,很多学者就开始探索公司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Griffin和Mahon, 1997),来证明或反驳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学者所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角度、衡量指标等不同,得出的研究结论迥异。总的来看,主要是有三个结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
2008年,沈洪涛、杨熠在他们的两篇研究里分别以1997—2003年沪深上市交易的所有非金融业的A股公司和1999—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石化塑胶业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企业相关利益者业绩指标衡量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在2002年发生了变化,即从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发展为具有价值相关性。姚海鑫等(2007)则以200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股东财富的关系,得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对股东财富具有积极作用。张雪南、郑碟(2011)以沪市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2009年年报中披露的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信息,研究了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其结果表明:企业对政府、员工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率与企业的价值呈正相关;而对投资者的贡献在短期来看虽然削减了企业的价值,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利于企业的未来价值。沈竹绮(2012)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赢得社会赞誉,形成企业的隐形核心竞争力,并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许叶枚(2012)认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而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外部收益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朱永明、安姿旋、薛文杰(2016)用2012—2014年已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第三方评级机构润灵环球(RKS)提供的社会责任评分研究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其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价值的实现,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并且企业社会资本能够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而与此相悖的是,李正(2007)以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扣除金融类企业以及年报等公开报告不全的公司后的研究样本为例,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进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两者负相关关系的结论。谭深和刘开明(2003)则在从国际竞争角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对外贸易的影响时,辩证地考虑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对外贸易影响的时间效应,认为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对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产生缩小效应,从而产生负面影响;而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则能建立企业的国际公信力,带来正面的贸易创造效应。
除此之外,仍有部分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以2000年之前上市的全部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样本总体和分行业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价值相关性不强,但是由于行业差异的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也不同。宋献中和龚明晓(2007)则选取了会计年报中具有代表性的17条社会责任信息项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参加中国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的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大。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顾湘和徐文学(2011)选取了沪市A股中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2007—2009年的报表数据,结合系统论、价值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股东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成明显正相关关系,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成负相关关系。王晓巍和陈慧(2011)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3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针对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不同,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度最大,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相互影响。杨汉明和邓启稳(2011)以2007年和2008年A股市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公司为对象,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利润率衡量公司业绩,用权益增长率考量可持续增长,采用指数法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并进行回归,分析了可持续增长、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企业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的结果。
本书认为,我国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之所以会得出如上三种不同结论的原因在于:①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评价上没有公认、通用的方法,而且多数学者在实证研究时所选取的数据和指标也不一致;②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时,很少考虑企业规模、所处行业、企业性质等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③未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时间滞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