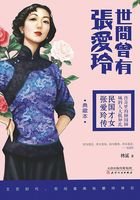
第8章 百媚芳华尘漠漠(2)
她的小说集《传言》和散文集《流言》一经出版,便一跃成为上海最畅销的书。《传奇》出版四天便再版。她自己创造了传奇。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在《天地》、《万象》、《杂志》、《古今》、《紫罗兰》等杂志连载多部小说。那时,她不过二十几岁,便迎来了大红大紫的人生奇迹。
她一生清高,孤芳傲世,却又这般迷恋尘世。她不肯锦衣夜行,不肯采菊东篱,她要的是风生水起。她并非不谙世事,也不是看不透现实,只是孤傲的心性令她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距离。她要的是生命的绽放,难免为自己的出名而沾沾自喜。每次,书被出版的时候,她都掩藏不住喜悦:
……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凹凸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工人道:“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
张爱玲红了,在这个没有生气,只有浮华的现实。她的书写尽了人性的冷漠,像饱经沧桑的老者。她不在乎是什么时代,也不在乎那些纷纷扰扰的议论,她只要创作,只要她的名字被人熟知。曾有一些学者和文人委婉地劝她不要随便发表作品,特别是一些背景不干净的刊物。张爱玲依然故我,一应“出名要趁早”的念头,美文如撒出去一把珍珠,引人注目。
读者被她的美文征服,以至于想看到她长的样子。出版社便顺应民意管她要两张照片。她不掩饰功利心,欣欣然答应。照片里她的笑带着藐视的意味,许是太过专注的缘故,只是那注视中流露着对世界难掩的恋慕。
政治于这浊世,有如魑魅魍魉,现实中的张爱玲是不会过问政治的,也不屑于政治,她要的只是出点名而已。她不想去招惹,更不愿被政治所陷。她不要人生与政治有什么相干。所以她不会为当时的日伪政权说什么话,她自认名气来得干净,像洗过的帕子,不怕日光的暴晒,因为没有污渍突兀地挂着。
然而,那世道,希图保持清高总是不易。张爱玲到底也没有逃脱日本人的垂涎。有一回,日方主持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她出席,她干脆地拒绝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谨辞。张爱玲谨上。”
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她爱出名,却不愿沾染政治,那个乌七八糟的文学圈,也素来是她不喜的。也并非是什么高尚的情操,是她孤傲,个人主义的表现罢了。她所要的是一个小说家的“俗名”而已,是一个凡人于尘世最浅薄的追求。以此挟持了她去装点政治的门面,是万万不能的。
只是,出了名,张爱玲的社交活动多了起来。她不喜交际,于不熟悉的人有种天生的抗拒。然而她还是要面对一些应酬,或许她也愿意在这个春风得意之时,领略出名的快意。
在那些场合,她不大随意,她孤僻的性子也不会为应酬而委曲求全,所以她话不多,也不会逢迎。她始终是她,来交际来凑热闹的,却又松弛不下来。她的文章打趣、俏皮,乐在其中,在人面前,她矜持自重。她又很狡黠,在她认为不太顺意的场合便带着炎樱和姑姑出席,即使成不了主角,被冷落了,也不至于太难堪。于是,张爱玲在那些场合里组成了自己的小天地,自娱自乐。
这是张爱玲的个性,她喜欢出名的风光,却又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这终究是她超脱世俗的执拗和“世俗进取心”的矛盾。
【落花飞雨】
张爱玲是喜欢苍凉的。她的一生演绎着苍凉,她的文字记录着苍凉。她曾说:“苍凉是更深长的回味,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用这种参差对照的方式写出现实的真实。在她的眼里,她所在的时代是沉重的,不容易大彻大悟。所以,她要写的是时代的负荷者,不是英雄。没有悲壮,只有苍凉,苍凉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曾郑重地说起这些对人生的思索。这些原本存在于心,原本与他人无关,然而她不得不把它见诸文字,起因来自一个批评的声音,针对她尖锐的批评。
在上海滩迅速走红,成就了张爱玲的瑰丽。在人们纷纷对天才女子予以浮华的赞美时,一个似乎不和谐的声音撞进来。
傅雷——一个追求完美的文艺批评家。他在张爱玲的《传奇》正畅销时,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其中对她的《金锁记》称赞有加。他说这本小说应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认为它的出现是个奇迹。
然而傅雷是苛刻的,他对《金锁记》的赞赏并不能替代他对其他作品犀利的批评。他认为张爱玲的其余作品缺少宏大的主题,有卖弄技巧之嫌,而且题材狭窄,不能够与《金锁记》相提并论:
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那噩梦中尽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灰暗、肮脏,弥漫腐烂、窒息的气味,如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死命挣扎,全无结果,无边的噩梦来袭,无从逃避。青春,幻想,希望都无身之地。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这些她小说中的场景,构成了一个社会。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只不可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
傅雷这段沉甸甸而尖刻的评论,像是张爱玲小说的注解,像是一面照出她文章灵魂的镜子。她隐隐地表达出的主题被他用言语道尽,什么都逃不过他犀利的眼睛。所以他无法容忍,写出了《金锁记》的天才作家在创作上出现的浅薄的错误。
傅雷最后告诫她:“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
傅雷的话如一记震耳的巨雷打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她正在被喝彩声包围,批评家的话便显得刺耳而引人惊诧。“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傅雷的这句话像一段判词,为她横空出世的传奇做了一个哲学的预示。张爱玲明白这话的分量,更明白这句话背后的严厉警告和深长意味。
但,她是矜持的,傲气的,她没有期期艾艾地解释、回应,也没有正面与批评家交锋。数月之后,一篇措辞委婉而目的明确的文章却见之于世。
张爱玲的这篇文章名为《自己的文章》,她在文章里表明了自己对文学的主张,透着不卑不亢。她解释,人生有安稳的一面,有飞扬的一面,前者却是后者的底子。人生的飞扬往往局限于时代里,人生的安稳却有着永恒的意味,即使被不断地破坏掉。
她终是认为宏大的主题与她不相干,她的骨子里是对人生飞扬一面的冷淡,她迷的是人生的安稳,在安稳中透出的普通而真实的人性。她的主题似乎是俗的,人性只有在俗中才能透彻地显现。她更像是一个临摹者,勾勾画画的不过是人性本来的面目罢了。
文章里,她说喜欢素朴。文章的华靡,是因为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素朴的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波光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
《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愠怒也没有嘲讽,不光明正大,也不卑躬屈膝,一如张爱玲淡漠的处世风格,只是依然无法掩饰她对世界的悲观: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设法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张爱玲的文字,是她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或阴暗,或凄厉,或混乱,由她对现实精准而深刻的印象与想象杂糅而成。现在这个世界被批评为残缺的,华而不实的,一个也许没有好下场的“奇迹”。
张爱玲似乎也没有完全置傅雷的批评而不顾,她曾言之凿凿地表示,不管已经连载的《连环套》被指出有多少弊病,小说仍会继续写下去。但事实上,这部小说很快就中断刊载了,张爱玲自己解释是“时间太逼促了,一期一期地赶”。
傅雷的这篇批评文章掀起了狂暴的波澜,似把张爱玲平稳前驶的艺术小船骤然卷到了起始的岸边,她自然不会因此搁浅,但这件事却成为她整个创作的一生中最戏剧的一幕。
在那个风烟渐起的乱世,人们还会为一个年轻女作家的作品而思索、批评、认真计较,本身来说,是对她的肯定。
张爱玲的天才在那个阴沉的乱世,似一朵奇葩,绽放独特的风姿。所以,她注定备受瞩目。
然而,傅雷的批评似一段谶言,张爱玲在《传奇》之后,较她整个的艺术创作来讲难有上乘之作。这似乎不只是创作灵感的枯竭,与她的人生境遇也有关联。
这是悲剧——张爱玲写尽了人世的苍凉,自己也难逃以苍凉终了,似哀怨的琴者,为自己的曲子所伤。尘世的乱象成就了她,她洋洋洒洒的文字把尘世捏成一个缩影,给世人上演一出出戏。那戏精彩、好看,像揭开了人生的幕布,把里面的脏、恶、丑倾倒而出。只不过,她自己也在这人生幕布的包围之中,她奋力地摆脱这不幸,但无济于事。后来,她清醒了,不再反抗,任凭岁月流转,最后,留给尘世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
苍凉,是这尘世的本质。每个生命轮回在尘世,都是苍凉而缥缈的一生。璀璨也好,崇高也好,都是尘世的片段,转瞬即逝,过眼烟云。却是苍凉浸透了每个生命的生与长,直至亡的过程。
张爱玲是对的,她说,苍凉是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启示。显然,她是悟了。只是她悟得尚不透彻。然而,倘若她悟得透彻了,于尘世又是悲哀的。言语路绝,心行道断,恐怕她便没有这千言万语话凄凉了。